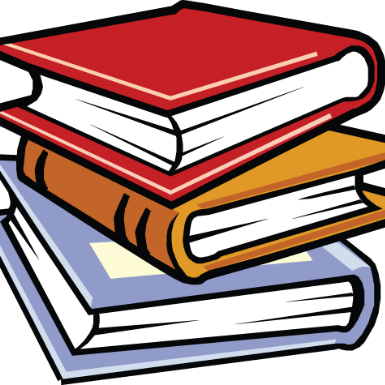我有些不耐烦,因为我害怕困意消失,而此刻的阳光正开始刺眼,它从树缝中穿出正好投射我的脸上。我站起身,企图将窗帘拉上,但是这个窗帘不管怎么拉都有一个缺口,我想如果这个缺口一直存在,我将心中难受,一夜无眠。我用了很多方式,发现始终没有办法将窗帘拉严实。我搬来一个椅子,打算站上去从最上面开始拉起。
珊珊此时又问一句,先生,你包夜么。
我有点心烦,说,我给你五十,你就给我站在这个缝前面给我遮光。
珊珊二话不说,站到了椅子上,顿时房间里暗了下来。我心中虽有感动,但更多鄙视,想这婊子真是为了钱什么都做得出来。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躺在床上拉上被子就打算睡觉。虽然我背对着窗,但我始终觉得奇怪,有个女的上吊似的站在椅子上,还不如让阳光进来。我未看珊珊一眼,说道,珊珊,钱是赚不完的,你早点回你自己那里休息吧,你年纪还小,不能满脑子只想着多赚一点是一点,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呢?你……窗户那边说道,因为我有了不知道谁的孩子,我要生下来。
我缓缓地转过头去,珊珊依然高高的站在原地,伸出手拉着窗帘,最顶上无法严合的那个部分透出最后一丝光芒,正好勾勒了她一个金边。随着窗帘微微的颤动,她的光芒忽暗忽亮。我看了半晌,说道,来,圣母玛利亚,你赶紧下来吧,睡床上。
第二天我们醒来已经是傍晚了。我打开小窗户,微风进来。我开始仔细打量着窗外,这是一个多么灰暗的小镇,我的眼前一片的灰瓦屋顶,沿着国道两边毫无美感的小店招牌,过往的货车司机正在挑选吃饭的饭店。一辆空载的卡车正在我们的楼下停车,儿童在卡车旁边玩着球。一列火车从百米外的铁轨上经过,我数着一共有二十三节。数火车是多么消磨时间的方式,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办法验算。但是何妨呢,恼人的时间在这一刻没有痛苦地过去了,而且全神贯注。楼下的儿童也和我一样在数火车,最后一节火车过去后,他转身对他的父亲说,爸爸,是二十四节。
他的父亲没有搭理他,继续指挥着卡车倒车。
珊珊醒了过来,冲到了洗手间去呕吐。吐完了以后问我,先生,你还要来一次么,不算钱,这个是算在包夜里的。
我点了一支烟,看了看她,旋即又掐了。我说,你怎么会不知道爹是谁呢,不是都有安全措施的吗?珊珊说,嗯,先生,我们这里除了半套和全套以外,还有一个叫不用套,再加五十就可以了。我估计是我吃的避孕药失效了。
我又把烟点了,说,那就是你活该了。你最好找到孩子的爹。你一个小姑娘,你怎么能抚养?
她说道,我能够抚养,你说,这孩子长大以后做什么呢?
我无意帮她规划未来。珊珊继续说道,总之,我不能让她干这一行。我再干这一行干十五年,正好能抚养她。你看,我现在一个月也能收入四千多,我已经攒了两万块,一万块可以生她下来,一万块算奶粉钱,可以养一年,我停工的那一年正好可以抚养她,然后我就得马上开工,我不能让人家知道我生过小孩。我干十五年,如果每年能赚差不多5万块,这个小孩子就能上学了,就是万一她有出息,考上了好的大学,我估计就吃紧了,最好还是得想其他办法再赚一点。我最怕就是开家长会,这个地方太小了,不能在这个地方上学,否则一开家长会,一看其他孩子他爹,弄不好都是我的客人。我还是换一个别的镇去。干几年就得换一个地方,否则别人就知道孩子她妈是干这行的。到了这个孩子十六岁,我还能养。
我说,你对未来的规划够仔细的。
珊珊摸了摸肚子,说,那是。我就崇拜我妈,我从小的心愿就是做妈。
我说,那你不知道这孩子的爹是谁,不是有点遗憾?
珊珊认真地反驳道,不遗憾,反正我从小的心愿又不是做爹。
此刻的阳光又要落下,我们睡的不巧,将白昼全部抹灭去。天空里的黑色浓墨一样化开。我问珊珊饿不饿,我不能整天都将自己闷在这样的一个空间,我需要开门,但我只是把自己闷到稍大的一个空间里而已,那些要和我照面走过的人一个个表情阴郁,但纵然这样,我也需要新鲜的空气。我顺手拿起珊珊的内裤,递给她,说,穿上吧,后会有期。
突然间,房门被踹开了,踹房门的力量如此之大,门框的木屑都飞到了窗帘上。门撞到了墙壁上又反弹了回去,门口传来一声哎呀。我还在想是哪个服务员这么豪放,至少有十个人破门而入。我都未及仔细看,被此起彼伏的“站住”“抓住了”“干什么”所包围,我早已经一动不动,周围的人还在源源不断地向我压来,我被第一个人反剪了手,脸被不知道谁的手按在地上,还有三只手掐着我的脖子,一个人的膝盖直接跪在我的腰上,两条腿分别被两个人按着,但是我感觉至少还有三个人要从人堆里插进来。我觉得很内疚,因为我身上已经没有什么部位可以供给他们制服,从他们进来的第一秒钟开始,我已经一动都不能动,但是他们却在我的身上不断地涌动,并且不断地大喊,不许动。
我从他们手的缝隙里看见了珊珊,她被另外五个人围在墙角。另外有一台摄像机高高举起,被摄影师端过头顶,在房子里不断地拍摄。珊珊抱头蹲在角落里,我见她扯了几把窗帘,我想她是要裹身的。旁边有人呵斥道,不要乱动,干什么干什么。珊珊继续拉扯了几下窗帘,气氛顿时紧张了起来,我这里感觉轻了一点,有两个人从我这里起身扑向珊珊,他们掏出手铐,直接把珊珊铐在了落地灯上,并且指着她咆哮,叫你不要乱动,你想要干什么,你想要干什么?老实一点儿。
我数了数,心想,可能这十五个人害怕珊珊用窗帘把他们都杀了吧。
气氛终于平静了下来,我又听到哎呀一声,周围取证的人们一阵骚动,结果发现是摄影师在叫唤。摄影师尴尬地看着大家,说,不好意思,刚才光顾着举过顶拍摄内容了,镜头盖没有开,只录到了声音,你们看行吗?
一个男子到他身边面露不悦,低声说了几句,转而对我说道,刚才我们这里取证发生了一点问题,现在我们要重新进来一次,你就保持这个姿势不要动,手里东西呢,你刚才手里东西呢?喏,在这里,你把这条内裤拿好,保持这个姿势不要动。
我指着珊珊问道,那她怎么办,她已经被铐起来了。
男子思索半晌,说,就这样,她不老实,万一跳楼什么的,女人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她就还是这样,铐在落地灯上。
我绝望地说道,那你们千万不要照着SM来处理我。人是你们铐的,不是我铐的。
男子踹了我一脚,道,话多。
说罢,他们全部退出房外。但是房间门已经完全不能关上,总是要往里开。摄影师掏出自己的手帕,压在门缝里。门终于关严实了。
一样的,门被刚才和我对话的男子重重踹开,但是由于之前已经踹过一次,连接处已经松动,这一脚直接把门都踹脱了门框,手帕飞了出来,在我眼前掠过,在空中完全地展开。我仔细看,手帕上绣了一个雷峰塔,正好落在我的脚边,我连忙拾起手帕,扔给了珊珊。珊珊接到手帕,迟疑着,因为她有三个要遮的地方,实在不知道遮哪比较合算。我大喊一声,遮脸。
旋即,我被一脚踢晕。
醒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审讯室。我的左侧脸颊挨了一脚,位置靠近太阳穴。我的泪水流了下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没有丝毫的伤心。我伸手抹去,发现是血迹,血迹怎么能从我的眼角流出?我要了一张餐巾纸。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总在冷笑的人,他见我醒来,第一句话便问道,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生日是多少?
我无力地回答道,田芳。
他一个暗笑,说,不对,她证件上不是叫这个真名。
我心想,真是王八蛋啊,这么难听的名字居然还是个艺名。我垂死挣扎道,我不知道,反正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就叫田芳。我该怎么处理?
他停下笔,看着我,说,劳教半年。
我说,有没有什么办法不劳教。
他说,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你签署一个合同,说你身体一切正常,以后如果出任何问题,和我们这次行动都无关。要不然就是劳教半年,但你如果出了任何问题,和我们这次行动也无关。签吧。这个是合算你了,你利用了我们执法中的漏洞。以后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我毫不犹豫地完成了这个交易。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从高墙里走出来更好,虽然外面也只是没有高墙的院子。墙壁上是斑驳的红色大字,我都不记得上面写了一些什么,应该是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和四个字。墨绿色的铁门就似我童年记忆里学校工厂的大门,我们常常去那里偷一些有趣的金属零件。我坐在对面的电话亭下面,想等珊珊从里面出来。不知道这个孕妇此刻在做或被做着什么。我想她只要亮明她的身体状态,她就能从里面出来。无论是多么面目狰狞的人们,除了他们指着鼻子骂我以外,我其实始终都能记得他们不经意间的叹息,我不认为那是人类在压迫下容易满足的贱,而是不经意间流露出来本是同类的交流。但当我想去挖掘的时候,大地马上就把井盖给盖住了,说,朋友,你想都不要想。
在等待珊珊的时光里,我顺着刚才的感触重新回忆了一遍我儿时的校办厂。
那是一个神秘的工厂。在我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儿童乐园,那时候我觉得它好大。一直到第一次同学聚会的时候,班级里最发达的同学站在六楼,看着儿童乐园,对我说,你看,我小的时候觉得我好大,现在一看,这个还没有我们家的院子大。小时候就是容易满足。
我在边上附和道,是那时候你人小,现在你人大了,参照物不一样了。
我小的时候在乡下,有一个车站,小时候走过去觉得好远,至少要走半个小时,后来我回了一次老家,没几步就走到了。那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步伐大了。
最发达说道,嗯,你这个提法很有意思,步伐大了。
在结束了这个现实的互相介绍自己的工作和职位的同学会以后,我一个人去儿童乐园里走了走,用步伐度量了一下,长四十八步,宽二十步,那是我小学里所有可爱回忆的所在,现在终于也变成了一个数据。我记得在一个阳光刺眼的中午,我爬上了滑梯的最高处,纵身一跃跳到了旗杆上,顺着绳子和旗杆又往上爬了几米,那是一个从来没有任何同学到过的至高点,我被飘扬的国旗裹着,眺望整个学校。
暑假就要到来了。
我艰难地挪动了屁股,视线从教学楼转到了厕所,没有什么好看的。让我来说说那时候我们的厕所,在这个最早的青春期里,我记得我们的便池和女生厕所的便池是背靠背的,当中隔开了一堵墙,那堵墙高两米。我量过。现在的我一度想过,如果姚明来我的学校大便的话,当他起身提裤子,他一定能看见对面。
那个时候上厕所,对面的对话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因为有两个通道,一个是头顶上的通道,另外脚底下便池也是通的,所以对面女生聊天都是立体声。由于一共有八个便池,所以是环绕立体声。她们聊天的声音多么甜美,内容多么无邪,音质多么悦耳,虽然还伴随着急切的嘘声。我曾经幻想,如果有那么一天,那堵墙倒了,将是什么样的情景啊。这个幻想在我小学的脑海里进行过几百次。
在旗杆上的我又挪了挪屁股,于是我看到了那一家校办厂。那时候的建筑在屋顶上有一个小天窗,天窗年久失擦,还长出了青苔,透过一点点能透过的玻璃,我看见里面的工人们都在紧张地忙碌。他们在一个长条的巨大金属桌子上打磨什么东西,那一定是很好玩的东西。
我正想着,突然之间一声哨响。我低头一看,什么都看不见——被我自己的脚挡住了,但是我听见体育老师刘老师的声音,他语速很快,说,同学,同学,你不要动,我们马上来救你。
我发现我的确已经不能动了,那是四层楼的高度,我已经不能再越回到两层楼高的滑滑梯上了。我的手也已经出了汗,要不是抓着勾升降国旗绳子的钩子,我估计差不多就以自由落体般滑下去了。老师们很快动员了起来,把我们所有跳高跳远仰卧起坐的垫子放在我的下面,刘老师负责稳定我的情绪,告诉我抓紧了,不要害怕,学校正在组织抢救。
我在旗杆上烤着,汗珠越来越大,脚也开始勾不住。我看了一眼教学楼,发现由于老师们都出来搬运垫子了,所以学生们都已经失控了,六层楼高的校舍走廊上,全部都是五颜六色的同学们和齐刷刷黑色的脑袋。
我的班主任看着垫子,小声说了一句,这个厚度不够,还是会出危险的。
刘老师拨开了班主任,说,如果这个小子掉下来,我会接住他。
不知道哪个看热闹看出了参与感的同学想出来要把自己的书包也垫在下面,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教学楼里一阵喧闹,所有的同学们都喊着,拿书包去救命,拿书包去救命。男男女女们都拎着自己的书包往我这里涌来。我们当时每个年级有四个班,每个班有五十个学生,一共有六个年级,总共一千两百名学生,累计一千两百只书包,在不到五分钟的时候堆在了一起。这些书包足足堆了三米多高。一千多个学生就围在儿童乐园的旁边,学校里广播不停地喊,请所有的学生回到自己的教室,请所有的学生回到自己的教室。但是没有一个学生回去。
老师们围成一圈正在商量,体育老师觉得,书包有软有硬,万一掉下来,脑袋砸在铅笔盒上也是一个悲剧,所以还是应该发挥垫子的作用。可是这些垫子现在被埋到了最底下,发挥不了作用,应该把这些垫子抽出来,然后放在最上端。
名著阅读 >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 > 第2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