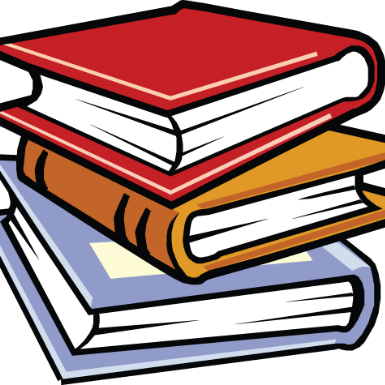这是南田县这几年来,出过的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案子,尽管上头说要尽量不外传,但这是个小县城,桥下摔死个人都有一拨拨的人要去看事后的热闹,更何况是这么稀奇的事儿呢?
罗韧多给了陈向荣一百块钱,让他打车回去,自己就不送了。
陈向荣挺高兴的,反正路不远,他把钱小心揣进内兜,一路走回去。
经过桥边时,和那些看事后热闹的人一样,他也探出头去,看了又看。
罗韧在车上坐了一会。
陈向荣不是他找的第一个人,在这之前,他和郑梨聊过。
郑梨挺紧张的,开始,大既以为他是来调查的,不住撇清和木代的关系。
“我跟她也不很熟的,”她说,“她到饭馆打工也才几天,她是哪里人,过去干嘛的,我都不知道,问了她也不说。”
但到底是个小姑娘,经不住他话里的试探和牵引,慢慢的,话里话外,都在担心木代了。
——“我木木姐身上没什么钱,我在长途大巴上遇到她,她就是那样,一个人,包都没拎一个。也没钱,后来姑妈给她支了点,但是也不多。”
罗韧听在心里:身上没钱的话,不大可能在短时间跑路。而且她那么明目张胆跳楼跑了,公安会有防范,第一时间会彻查进出的车站,所以木代现在的位置,最有可能还是在南田。
“她在南田,还有什么朋友吗?”
郑梨想了一下:“没有。她也没说起过她家里人,只说有个男朋友,人长的帅,好像也挺有钱,对她也好。”
罗韧心里,某个柔软的角落,动了一下。
“她一直要找人,说是二十多年前住在拆了的老楼里的,一个喜欢穿红色高跟鞋的女人。不过好像也没找着。”
从郑梨这里,似乎也得不到更多信息了,离开之前,罗韧最后问了一句:“她精神状态怎么样?”
郑梨听不懂。
罗韧换了个问法:“你觉得,你木木姐,是个什么样的人?是厉害呢,还是软弱的那种?”
郑梨说:“我木木姐怎么可能软弱,她可厉害了。”
想了想,又补充:“我也说不清楚,有时候你觉得她凶吧,转头她又会对你很好。就是那种,外头是硬的,里头是软的的那种。”
罗韧开着车,在南田县兜了一下午的圈子,每条街每条巷都经过,不止一次。
有时停车下来买杯东西,转身又扔掉,城郊也去了,车子飙过去,一路的尘土。
他有点怀念在小商河时,一路飙过戈壁,沙丘冲浪,旋车激起扬沙,嗖呦一下,像扬起的风。
他一直兜圈到很晚,然后去了夜市,买了些日用品,买了酒,啤酒、白酒,荤食,烤鸡、烧鹅、盐虾,几样拌素菜,装了白饭,经过水果摊时,又买了几样水果。
然后开车,进了白天兜逛时看中的小旅馆。
是真小,简陋,也没什么人,身份证登记是用手抄的,也没有什么摄像头,洗手间甚至不是燃起热水,是热水器,要用烧的。
罗韧入住,先烧了水,然后开了电脑,定了网页,最后把饭食在桌子上摆开,并不动筷,打开了电视去看,信号也不好,屏幕在跳,沙沙沙的杂音,当地的新闻碰巧在报昨天的案子,主持人抑扬顿挫地说:案情已经取得重大进展。
夜半12点过,有节目的频道都少了很多,罗韧随便揿到一档情感节目,播的是见惯的原配与外遇之争,面部打着马赛克的男人稳坐钓鱼台,原配泣不成声说:“当年你追我的时候,也是掏心掏肺……”
嗯,昨日掌中玉,今日口中痰,两相撕破脸皮,恨不得唾在地上。
有叩门声,很轻,夹在主持人苦口婆心的叨叨中。
罗韧却立时警醒,下一刻关掉电视,顿了一顿,走到门边,伸手搭住门扣,轻轻拧开。
晕黄色的走廊灯光下,木代就站在那里,总觉得她好像更瘦了,带着很大的口罩,只露出两只眼睛,像虽然受了惊吓但没有恶意的小动物,眼睑下睡眠不足的暗影。
她说:“我看到你的车,在街上转啊转的,我想,你大概是来找我的。”
罗韧向前走了一步,木代很敏感,马上后退。
罗韧笑了一下,说:“木代,我之前搂过你、抱过你,也亲过你,你要是觉得这病是近距离接触就能传染的——现在才防范,是不是太晚了些?”
木代没说话,头略略低下,长发从前头拂下,露出细致白皙的脖颈,苍白的,又脆弱,好像一不留神,就会折断了一样。
罗韧问:“这两天吃饭了吗?”
她想了一下,然后摇头,衣服有几处蹭破了,破口边缘还有灰,也不懂她这一日夜,是藏到哪去了。
罗韧伸手,拉住她胳膊进来。
屋里的味道不同,食物的香气,刺激着闭缩了好几顿的味蕾,木代的目光落在那一桌子夜宵上,大都是塑料餐盒盛着的,但于她,已经是铺开的盛宴了。
目光被隔断,罗韧站过来,挡在她和里屋中间,示意了一下洗手间:“洗澡。”
木代说:“我没有衣服换。”
“我听说了,一件行李也不带,一分钱也没有,带了脑子带了手,自己觉得挺潇洒是吧?”
他拿了衣服给她,男式的,还有超市里买的一次性旅行换洗内裤。
然后推她进洗手间:“洗澡,洗完澡吃饭,然后说事。”
☆、109|第①③章
郑水玉家的洗手间只巴掌大,用水又俭省,不知道每天是不是按照配量来,水头从来小小,每次洗完澡的感觉,都像久旱的地才湿了表皮,浑身不舒服。
所以,这大概是这些日子洗的最舒心的澡了,水量充足,水温也滚烫。
擦干了身体出来,先撕开包装穿了内裤,又抖开罗韧的衣服看,半新不旧,叠痕整齐,凑近了,还能闻到洗干净的衣服特有的味道。
比划了一下,真大,衣袖长出她胳膊一大截,直接套头进去,整个人像罩了个麻袋。
她低下头,袖子裤脚都连挽好几道,才打开门出去。
走到桌边坐下,筷子就在手边,木代犹豫了一下,觉得宾主毕竟有别,还应该等罗韧说一声再开动。
谁知罗韧先把笔记本电脑先递过来,说:“先看完。”
木代接过来,屏幕往下压了压。
两个打开的网页,两篇文章,都是讲艾滋病的,关于原理、症状、潜伏时间、传播途径等等。
她手指滑在触屏上,一下下翻着看,头发上的水滴在泛亮摁键边上。
看完了,她把电脑递回去,罗韧接过了放在一边,说:“今天我问过了,中心院就可以做抗体检查,你要是不放心,找时间我给你抽血,然后送进去验……先吃饭吧。”
木代闷头吃饭,人也奇怪,开始饿过劲了,什么都不吃也不饿,真的开始有东西裹腹,反而越吃越饿。
中途罗韧开了酒,木代自己拿了罐啤酒,咕噜噜一口下去一半。
据说长的饭局总有一两个停点,通俗讲就是“吃累了,歇一歇,再战”。
这半罐酒就是第一个停点,木代把啤酒放回桌上,筷子也搁下,沉默了一会才问:“大家都还好吗?”
“挺好。”
“凤凰楼……开张了吗?”
“开了,当天下大雨,一桌客也没有,曹胖胖差点哭了。”
木代想笑,笑容刚出现就隐了,总觉得好多糟心的事好像在边上虎视眈眈的脸,说她:还有心情笑!
又问:“那凶简呢,现在应该第四根了吧,凤凰鸾扣有指引吗?”
罗韧说:“没人关心凶简。”
这话是真的,每个人都在自然而然的懈怠,总觉得凶简这事虚无缥缈、师出无名、无关痛痒、并不迫在眉睫,无利可图又凶险莫测。
做一件事,要么有动机,要么有动力,他们都没有——神棍形容的没错,就是拉磨的驴,鞭子不抽的狠了,不切实吃点亏,都是不想动的,炎红砂因为新奇好奇成立的“凤凰别动队”,过了起初那股子劲,现在挺有各回各家的架势。
更何况,现在有更紧迫的事情。
罗韧终于问到正题:“为什么要跑?”
木代没吭声,过了会把啤酒拿起来,又灌了一大口。
“头脑一热,看到开着的窗户,觉得能跑掉,就跑了。”
罗韧说:“起初,你很配合调查,要想跑的话,在饭馆时就跑还更容易些,犯不着到公安局才跑。”
“木代,你是害怕了吧?”
木代不说话,过了会,她把面前的碗盒推开,胳膊撑在桌面上,垂着头,双手捂住了脸。
罗韧听到她吸鼻子,鼻尖泛着红,轻轻咬着嘴唇,但是不拿开手。
她不像从前那样想哭就哭了。
罗韧把抽纸盒推过来,说:“别慌,任何事情,都是可以解决的。”
木代没看他,还是低着头,伸手抽了一张,胡乱擦了擦脸,然后揉了团扔进垃圾桶。
“有目击证人,我开始跟他们说,半夜发生的事,天那么晚,马超可能是看错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笔录的时候,第二个证人隔着玻璃看过我了,也说是我。”
说着又去拿酒,罐里差不多空了,拿起来很轻,一摇哗哗的响,只好又放回去。
其实还有白酒,但是罗韧先不给她开。
他又问了一遍:“那你害怕什么?”
木代低着头,说:“那天晚上,我睡的很好,连梦也没做一个,特别沉,所以,连我自己也不确定……”
罗韧接过话头:“你害怕是自己睡熟之后,无意识的状态时,曾经起身出去过?”
木代说:“因为我有前科啊,何医生说我人格混乱,有时候我自己做的事情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现在已经给自己定罪了是吗?”
木代不承认,也不否认。
她想着:有两个证人呢。
一个叫马超,是张通的混混同学,一个叫宋铁,是五金公司的职工,两人并不认识。
两个证人,证词互相印证,都在当夜看到她,连她身上穿的那身衣服都说的确切。
罗韧笑起来:“木代,我教你一句话,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掉泪。”
木代抬眼看他:“什么意思?”
“别想着自己是个罪犯,先入为主你就会忽略很多重要细节。我是之后才来的,不可能知道详情,当天的事情,要靠你去分析回忆。”
他取出那瓶白酒,也不用开瓶器,桌角一磕磕掉瓶盖,拿了一次性的杯子,倒了十个小半杯,又掏出手机,调到秒表。
“咱们来做个游戏,你现在为自己辩护,你就想着自己是被陷害的,要尽力为自己开脱,给出让人信服的理由。两分钟一条,时间到了,想不出来,就喝酒,一条都想不出来,那行凶的就是你。”
他揿下开始,2分钟倒计时,上头的数字开始疯狂变换。
木代用了好一会儿去消化他的话,没来由的紧张,目光触到罗韧的,他神色凝重,催促她:“赶快!”
连这语气都加重她紧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