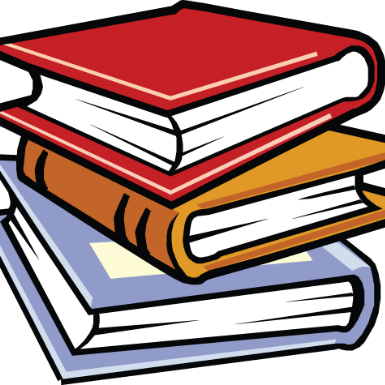“我弥补不了什么了,死人不可能活转过来,我那时候的兄弟,也只剩下你了。你回去,跟由纪子求婚,好好过日子,生很多孩子,子孙满堂,活到牙都掉光了——这样的话,不管到时候我活着还是死了,我都多点欣慰。”
他握起拳头,送到青木面前:“来,答应的话,碰个拳。”
青木不干,低着头,牙关咬的死紧。
罗韧说:“不碰吗?我有的是耐心。”
青木抬起头,看到罗韧在笑,只是,那笑容似乎越来越模糊,一股晕眩之意涌上颅顶,青木想说什么,只张了张嘴,来不及说话,就一头栽倒在地。
罗韧没去扶他,他脸上带着笑,缓缓放下伸出的拳头,说:“我早就知道,光凭灌酒,是放不倒你们的。”
他看着青木喝下了那杯水,又寻衅跟他打了一架——适当的剧烈运动有助于药效的加速发挥,一切,都拿捏的刚刚好。
——罗,算我一个。
——也算我一个。
当年,他本不该,带任何人去的。
罗韧拍了拍伏在地上的青木的肩膀,又交代了他一次:“回去跟由纪子求婚,好好过日子,生很多孩子,子孙满堂,做个哪怕牙齿掉光了,都还能跟人打架的老头。”
他疲惫的,撑着地站起来,捡起那把枪,然后关了灯,在黑暗里,慢慢地走了出去。
一个小时之前,罗韧收到了猎豹打来的电话。
——“罗,我们该见面了。”
——“一个人来,开着你的车子,到古城南门的十字路口,等我电话。”
回到房间,揿亮灯,灯光下,屋子的正中,站着一个人。
郑明山。
罗韧对着他笑笑:“来啦,挺快的。”
说完了,倒转那把枪的枪口,递了过去。
郑明山接过了看,拆卸枪管和弹匣:“超微型冲锋枪,配子弹,枪口附近声响可降至80分贝以下,黑格勒科赫公司原产,改装过,类似沙漠杀手乌齐枪。”
罗韧拆开绷带:“大师兄很懂。”
郑明山冷眼看他用军用粘合剂封住伤口:“留下自己的兄弟藏起来,反而跟我合作?”
罗韧答得平静:“在菲律宾跟着我出生入死的兄弟,只剩这一个了,大师兄让我留一个吧,这样的话,死去的兄弟们在地下也心安。”
郑明山没有说话,罗韧的意思他懂,很久以前,他出危险任务时,也会跟兄弟们说:大家伙不能全死,一定得留一个,往后后,给咱们上坟、烧纸、送烟,还有过好日子,都靠这一个的念想啦。
罗韧吁一口气,腹部绷住,重新包扎伤口。
郑明山开口:“我小师妹不能死。”
“我懂。”
“为了我师父,猎豹必须血债血偿。”
罗韧笑:“猎豹也是我的目标,必要的话,我跟她一起死。放走了她,我身边的人永远不会安全。”
他呼气、吸气,测试包扎的妨碍度,然后从药瓶里倒出胶囊药丸。
郑明山皱了皱眉头,没忍住:“药物肌理和神经性兴奋剂不要经常吃,杀人一万,自损八千。”
“只这一次。”
他穿好衣服,起身去到洗手间,拧开龙头,冷水激脸,郑明山抱着手臂,倚在门口看他:“我联系上朋友了。”
“国际刑警那边的消息是,没有针对猎豹的任何抓捕和通缉,因为一年多以前,内部消息显示:此人不再具备行为能力,对他人和社会不构成任何威胁。”
懂,她受过致命性伤害,但凶简让她东山再起。
罗韧沉吟了一下:“所以他们不会帮忙?”
“指望不上。就算愿意私下援助,时间也来不及。”说话间,他递过来一个gps定位微型追踪器,“另一个朋友倒是可以远程在线援助,你出发之后,带上这个,他会帮我确认位置。”
罗韧接过来,想了想,缓缓摇头:“光靠这个不行,猎豹很小心,类似的电子件,我怕是带不进去。到时候,咱们可能得靠最笨的方法——请你的朋友设法黑入沿路所有的联网城市摄像头。”
郑明山点了点头,停顿了片刻:“还有就是……猎豹是带了手下的,我觉得,多带点人手,方便行事。”
罗韧盯住郑明山,一字一顿:“不行。”
“这个你说了不算,师父被绑架了,他做小徒弟的,不应该做点什么?每天嚷嚷着姐妹情深的,不应该做点什么……”
话没说完,罗韧已经冲上来,一把揪住他衣领,恶狠狠道:“不行。”
郑明山被勒的有点透不过气:“来来,先松开。”
罗韧齿缝里迸出话来:“郑明山,我跟你合作,是因为你是木代大师兄,我去救她,没资格绕过你。但红砂、一万三、曹胖胖,他们跟我们不一样,他们连枪都没见过,你没权力把他们带到那么危险的地方去!”
郑明山想了一下,说:“行吧。”
又不耐烦地推他手:“松开松开,勒死了都。”
罗韧松开他衣领,最后交代:“猎豹这个人很狡猾,我不敢肯定她会不会真的露面。整个过程,咱们也没法互通讯息,一靠见机行事,二靠……老天给运气。”
他似乎很多话想说,但又忽然卡壳,末了笑了一下,转身下楼。
郑明山目送他背影,忽然叫他:“哎,不去跟隔壁……告个别?”
罗韧脚步不停,也没说话。
郑明山想了想,又叫他:“哎,罗韧,如果你和我小师妹都活着回来,我会考虑把她嫁给你。”
走到楼下的罗韧忽然停住,然后抬头看他。
郑明山正趴在栏杆上,身后亮着屋里映出来的灯光,低头看着他,说:“我觉得男人吧,能不离、不弃,明知有危险还为了她上,就足够了。你看,我对男人的要求,从来都不高的。”
罗韧哈哈大笑。
发动车子时,少有的,也同时开启了车顶的狩猎灯,强光在黑暗中打出去,照出一条亮的炫目的路来。
曹严华打着呵欠,脚边蹲着曹解放。
往常,曹解放都是在楼梯下头自个儿的“豪宅”睡的,但今儿个被神棍那一弹弓打的痴痴呆呆,曹严华不放心,睡觉的时候把它搁床边了,郑明山喊门的时候,他睡眼惺忪披上衣服就往外走,低头一看,曹解放也迷迷瞪瞪梦游一样跟着他。
大家伙在聚散随缘的大堂里围坐了一圈,除了他,被叫起来的还有一万三、炎红砂、神棍,每个人都是睡眼迷瞪,脑袋点巴的比曹解放还像鸡。
这啥意思啊,半夜三更的,开会啊?
郑明山笑了笑,把面前的笔记本电脑翻转了给他们看,屏幕上的画面,像素不是很清楚,像摄像头的街景,十字路口处,停了一辆悍马。
曹严华先认出来:“这不是我小罗哥的车吗?”
郑明山嗯了一声,开始从头讲起。
曹严华的睡意就在郑明山的讲述里消失的无影无踪,渐至毛骨悚然。
郑明山的最后一句话是:“所以,罗韧不让你们去。”
曹严华脑袋轰轰的,觉得血管里的血都烧起来了:“我要去!那是他女朋友,可也是我小师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他跟我小师父证都没领,要论亲疏关系,我比他还近呢。”
炎红砂想了想,眼圈泛红,说:“大师兄,罗韧这情,我们是领的。危险是真危险,这种场合,你们比我们专业。但是,我们不能什么都不做,就在这干坐着啊。说句实在话,你们不会总都枪来枪去的,真到了拼拳脚的时候,我在边上,使阴招都能帮得上忙呢。”
神棍居然很兴奋:“就是就是,我可以躲在边上,发暗器啊!”
郑明山笑起来,说:“就是这话。我不是想让你们去冒险,但我跟罗韧不一样,这些年,要不是有我的兄弟前后策应,我早不知道死在哪了。我喜欢别人帮忙,越多越好。没有一根钉子是废的,没有一个人是没用的——多带一个人就是多一分力,关键时刻,跑个腿、报个警、吼一嗓子都是好的。”
曹严华点头:“就是就是,带我和红砂去。神先生和一万三就留在这儿,当后勤好了。”
一万三不干了:“凭什么留我啊?”
“你又不能打,打起来又不能跑,带了有什么用?”
说着又看神棍:“神先生,不是我说你,你那暗器的准头,没准猎豹还没动手我们先被你消灭了。而且……有些事,总得有人张罗的。”
他话里有话,指的是凶简的秘密,总得留个能主事的人。
一万三气的不行,忽然想到什么,心里一动,先不说,预计临门一脚再放杀手锏。
就在这个时候,炎红砂忽然紧张地咦了一声,急指电脑屏幕:“快看!”
画面上,有一辆车对向驶来,就停在罗韧车边,罗韧下车了,有两个人手持类似安检检查仪器的东西对他上下扫描了一遍,从他衣服上拽下了什么。
郑明山心里骂:妈的。
罗韧的顾虑果然没错,什么通讯设备、电子件,都是别想带进去的。
然后,罗韧被带上了那辆车,开走了。
郑明山精神骤然紧张,看曹严华和炎红砂:“那就这样定了,我现在出去搞车,你们马上收拾,带上自己最趁手和利索的家伙,记着,可能要打场硬仗。”
他迅速离开,曹严华和炎红砂无端心慌,快速而又尽量轻声的回房,曹严华一走,曹解放就跟着了,惜乎曹严华跑的快,曹解放跟的慢吞吞的,才跟到一半,曹严华已经折返了,曹解放又慢吞吞的转向,跟着他回来。
他额上汗津津的,拿了开锁的工具包,一万三鼻子里哼一声,说:“哈,哈。”
言下之意是,这玩意,能用上个毛。
炎红砂也下来了,拎着一圈特制的绳子,她也不知道什么叫“最趁手、利索”,从小,炎老头就训练她下井,她在绳子上有功夫,这绳子的韧性和抗磨度都是顶尖的——谁知道会遇到怎么个状况呢?带上吧,没错的。
门外传来车声,郑明山不知道从哪搞了辆白色小金杯来,曹严华和炎红砂慌慌张张上车,车门尚未关严,一万三忽然慢条斯理来了句:“你们确定,这一趟用不着我的血吗?”
郑明山听不明白,曹严华和炎红砂却是心里透亮:猎豹的身上有凶简,万一最终对付时,又要用到五个人的血呢?
一时间来不及去找什么针管,曹严华又把门打开:“上车上车。”
于是,大门口只剩下了神棍和曹解放,一人,一鸡。
神棍低头看了一眼曹解放,曹解放也看了眼神棍,就在这么无言的对视当中,车子发动了。
这蓦然发动的声音忽然间惊着了曹解放,它如同大梦初醒,浑身的毛噌一声奓起,脖子一仰,一声嘹亮的:“呵……哆……啰……”
再然后,它翅膀乱扑,如同离弦的箭一般扑将出去,又像是出膛的炮弹,好巧不巧,一头从开着的车窗里撞了进去,恰似愤怒的小鸟,在不大的车厢里一阵乱飞乱撞。
鸡毛飘飘悠悠落下。
卧房里,睡的半醒的张叔不耐烦地翻了个身,拽着被子蒙住脑袋,含糊不清叨叨:“破鸡,又叫……改天煮了……”
一万三淡定地从脑门上拿掉一根鸡毛,说:“行了,带上吧。”
是他们考虑不周,曹解放当然是宁死也不跟神棍这个打鸡又嗜爱肯德基的终结者待在一起的。
车子驶将出去,一万三抱着电脑,紧张地查看监控变换的画面,还没来得及定神,伴随着刺耳的刹车声,他一头撞到了车前椅背上。
一万三痛的怒喝:“又怎么了?”
郑明山踩着刹车,透过前档玻璃,看不远处摔倒在地的青木。
那杯水泼了大半,剂量也少了大半,他比预计的醒来时间要早很多,脑子昏沉沉的,只记得有事要做,拼命挣扎着爬起来,咕噜噜灌了一肚子凉水,又浇自己一个满头满身凉,然后跌跌撞撞地出来。
炎红砂小声说了句:“是那个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