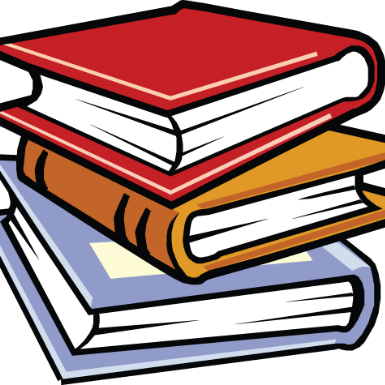郑明山嗯了一声,屁股兜里掏出个瘪瘪的烟盒来,似乎是想抽,忽然想到这是重症监护病房,又把烟盒塞了回去。
“真话?能承受?”
木代转头看他,用力点头:“我能。”
郑明山看她。
以前,梅花九娘跟他讲起这个小师妹,总是一脸的微笑和纵容,说:“木代这个小姑娘啊……”
现在,他不敢讲她是个小姑娘了,她站在他面前,被数不清的事情磨砺过和磨砺着,磨去了表面的那些稚气、天真的想法和不成熟,渐渐支楞出她自己的风骨来了。
和梅花九娘一样,她也是个硬骨头。
郑明山说:“那我就讲实话。老实说,见到罗韧的时候,以他的失血量、受伤程度,依我以往的经验判断,属于抢救不过来——他早该死了的。”
木代的牙齿死死抵住嘴唇。
郑明山耸耸肩,食指屈起,磕了磕探视镜:“但是你看,他到现在还好好的躺着,你问罗韧还有没有希望,其实从那个时候起,老天就给你希望了。只不过这希望像个小畜生,咱也不知道它会不会中途夭折,能不能养的大。”
末了,他伸出手,按住木代的肩。
“尽人事,听天命。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准备。这世上那么多人,失去爱人和亲人的,远比你想象的多,你不是最倒霉的哪一个,也不会最幸运。罗韧回来了,你就好好过你们俩的日子。他回不来……你就好好过你的日子。”
说完了,径直转身离开,没再看她,他不擅长应对这种场合,也不擅长安慰人。
他也不想罗韧走,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这个世界那么庞大,个人那么轻渺,每天都有人出生,又都有人看不到第二天的太阳,凭什么你就一定幸运?凭什么你不会倒霉?
老天对人本没有安排和设计,何时登场,何时落幕,都是一团胡写的杂乱无章。
他一直走到走廊尽头处才停下,点了烟,抽了一口,又慢慢吐出烟气。
这时候,要是有二两小酒、猪头肉,或者花生米就好了。
身后传来脚步声,是青木。
郑明山吁了一口气:“我就不跟我小师妹道别了,跟她说一声,我还要回去处理师父的丧事,让她不着急回去,先顾着罗韧,活人……总是比已经没了的人重要。”
☆、195|第③章
有些话,说出来或许伤人,但却是真理。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依着亲疏关系的不同,你这里的天崩地裂,在不同的朋友那里,变作了屋舍崩塌、房顶漏水、夜半时的辗转反侧,闲暇处的一声叹息。
第三天,聚散随缘开门营业,用张叔的话说,地球照转,生意照做。
第五天早上,木代推开房间的窗户,看到曹严华在楼下吭哧吭哧压腿、下腰、三步上墙。曹解放优哉游哉地在水槽里喝水,间或抖罗一下翅膀,浑身的毛奓起,像是在伸懒腰。一万三肩上挎着红白蓝塑胶袋,左手拉着折叠小推车,迎着阳光往菜场去,楼下,张叔的大嗓门经久回荡:“大白菜、排骨、土豆,还有盐,有上好的黄酒,也买两瓶!”
炎红砂也忙活起来了,扫地、擦桌子,脏活重活抢着干,张叔眉开眼笑夸她的时候,她很是严肃:“张叔,不白干,公平交易,得给我开工资的。我是要还债的人。”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焦虑,她念念不忘,要帮炎老头和叔叔炎九霄还掉那笔身后的债。
神棍也暂时离开,去附近另一个古城的好朋友那小住,用他的话说,在这里“研究”没有进展,他住的别扭。
不过临走之前,他总算是说动木代和炎红砂,去到那个收有凶简的小屋里,又做了一次水影的尝试。
这一次,虽然罗韧还是缺席,但得到的图景和信息,比之前那次,还是多的多了。
街巷,类似天桥耍弄的把戏,铜锣震响,草台班子拉开,好多洋气稀奇的节目儿,猴儿算术,老鼠抬花轿,不过,最最开眼的,是狗识字。
一堆写了大字的斗方纸杂乱排开,那狗低着头,狗爪子刨刨,低头嗅嗅,依次叼出了“恭”、“喜”、“发”、“财”四个字。
有个观者起哄:“这个不算,狗鼻子灵,谁知道是不是纸上掺了味儿!”
班主陪着笑:“那哥儿想怎么样?”
“让我来写字,这狗要是还能认出来,那才叫一个服!”
旁观者并不同意:“那不行,谁知道你是不是跟班主串通好了,演戏儿的!”
换言之:万一你是个托儿呢?
班主向着人群团团拱手:“那大家伙给支个招?”
有人提议:“让咱垄镇私塾里的卫老夫子给写,那不就公平了?”
说着便跑开去,过了会回来,身后跟了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葱绿色的琵琶对襟衫子,大眼睛,因着女儿家的好奇心性,白皙的双颊上泛着红,手里头拈了张写满字的字纸。
人群鼓噪着给让开了一条道,又重新围拥过来,什么都看不见了,只听见一浪赛一浪高的叫好声,那里头的表演,定是博得了满堂彩。
……
听了他们对水影的转述之后,神棍皱起眉头。
说起来,那些所谓的猴儿算术、狗儿识字,就像现代的魔术一样,内里都是有玄机的。
比如猴儿算术,几只猴儿抢答,班主出了个题,一加一等于几?喏,那个赖皮猴儿举手了,比了个二。很好,赏香蕉一根。
而实际上,那猴儿才不懂加减乘除,它平日里是被训练着比二,瞅班主时,看到班主的教杆对着看热闹的人群,但教杆下的手指却是对着自己的:懂了,是自己答,于是赶紧比了个二,不比的话,要挨鞭子呢。
所以,这些耍江湖把戏的,是断不敢把控制权交给不懂行起哄的人的,这样一来,立马乱场穿帮。
猜不透,这水影里的把戏,有玄虚。
屈指一算,七幅水影才能凑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还差着一幅呢。
或许,尹二马那的七根钥匙,汇合了只有木代知道的师门秘密,才能开启进一步的线索,但是,罗韧现在的情形,连郑明山都发话让木代“不着急回去”,他们哪好意思开这个口呢。
神棍想了想,有点不甘心:“那银眼蝙蝠,没你的话,能飞吗?”
他寻思着:即便木代不能同行,自己先过去也行啊。
木代看了他一眼:“你说呢?”
也是,鲁班这样千回百转的心肠造出来的稀罕玩意,哪能见人就飞呢。
一时间没进展,只好暂时“隐退”,临走前,把曹严华拉到边上吩咐:“你有点眼力劲儿,没事给小口袋敲敲边鼓。七七之数呢,这小萝卜要是三年五载的醒不来,凶简就这么不管了?”
……
罗韧昏迷之后的第七天,凤凰楼开门了。
经历过罗文淼的横死和聘婷的久病,郑伯比其他人都看的更开些,他心平气和地腌制着当天要用的羊腿,对过来帮忙的木代说:“罗小刀虽然留下不少钱,但是坐吃山空。医院里的费用那么贵,他要是一直醒不来,费用就是大问题,我们得考虑持续有进账不是……”
……
你看,即便有人的人生停滞,大部分人,还是要继续生活。
木代也好像很快恢复,早上起来,会教曹严华练功,不再是那些似是而非的招式了,教他一整路的功夫,陪着他练,一招一式,分解给他看。
凤凰楼和酒吧,她两头帮忙,有人跟她说话,她就很淡的笑一下。
只是饭吃的少,坐到饭桌前,会把盛好的饭再倒一大半回去,跟霍子红解释:“红姨,我吃不下,吃多了,饭好像堆在嗓子口,气都喘不过来。”
菜也很少动,你要是说她,她就会咬着筷子说:“有点腻,吃下去心里难受。”
她越是平静,霍子红就越是慌,专门把她拉到一边说话,说:“木代,不管罗韧出什么事,你千万不要想不开啊。”
木代笑起来,说:“红姨,我不会想不开的。师父交代我的事,我还没做完呢。我出事了,大师兄还有红砂她们,都拼了命的救我,我要是想不开,就太对不住人家了。”
说完了,拍拍霍子红的手,转身离开去忙自己的,霍子红怔愣着站在原地,想着:这小丫头,什么时候这么懂事,这么会说话了呢?
与一万三他们隔两天去看罗韧不同,木代每天都去。
只来回这么几次,医院就熟悉的像家一样了。
到的时候,如果赶不上探视时间,就隔着探视镜,呵一口气,用手指在镜面玻璃上写各种各样的字。
有一次,小护士跟她开玩笑,说:“你这样写啊写的,时间长了,说不定玻璃都让你写穿了。”
说完了,忽然发觉这玩笑开的不好,好像是咒人家永远醒不了,尴尬地笑着离开,下次再见了木代,下意识躲着走。
木代其实并不放在心上。
而如果能赶上探视时间,她就会在病床边一直坐着,每到这个时候,青木就会在探视镜外盯着,他在这里没有家,没有杂务,吃住都在医院,反而能做到24小时陪床。
木代一来,他就紧张,或许,还在担心着她那被洗脑之后隐患式的“忽然爆发”吧。
离开之前,木代会轻轻抱一下罗韧,贴贴他的脸,在他耳边喃喃的说几句话。
这时刻,是她一天中,最放松,也最疲惫的时候。
她说:“罗小刀,你睡一时可以,不要睡太久了啊。我很担心,万一哪一天,我习惯了,也懈怠了,十天半个月才来看你一次,可怎么好啊。”
抬起头,看到外头的青木,紧张的脸都绷起来了,木代觉得,罗韧有这样的朋友挺好的,也觉得每天就这么逗青木一下,也挺好玩的。
出去的时候,她对青木说:“你担心我杀了罗韧吗?要是担心的话,你别站在外面啊,我手快,抱他的时候给他一刀,你站在外面,来不及救的。”
青木尴尬的说不出话来。
木代说完了,哈哈一笑,不再理会他,双手插在兜里,慢慢地下楼去,她不喜欢坐电梯,狭窄的空间,太气闷局促,她一个人走楼梯间,一级级数台阶,听自己的足音,想着:要累积满走了多少级,罗小刀才能醒呢?
一楼的走廊里,有个宣传橱窗,叫病友园地,每两天更换一次内容,木代习惯在经过的时候停下,仰着头看。
里头的内容其实寻常,什么应季养生小秘诀,预防脊椎病的三点注意,久卧病人如何防治肌肉萎缩等等,年轻人一定不感兴趣,因为木代每次看完了想走,总会发现身边站着的,是一些老头老太。
她慢慢走回酒吧,路上消化着自己看到的内容。
——原来夏季应该多吃苦味,比如蜂蜜苦瓜,以后她持家了,罗小刀听话,吃苦瓜的时候给蜂蜜,不听话,吃苦瓜的时候只能拌苦瓜。
——久卧的病人,如果长久不动,肌肉会有一定程度的萎缩,也不知道罗韧还要躺多久,下次来,她带个小锤子,锤头包着棉花布,帮他敲敲腿,敲敲胳膊,啧啧,罗小刀多会享受,这是旧社会地主老财的生活呢……
游人如织的景观路上,她咯咯笑出声来。
回到酒吧,生意似乎不忙,她先回房,一级级顺着楼梯上去,到转弯处时,红姨和炎红砂正下楼,木代笑一笑,低头让开条路,霍子红忽然失声叫了句:“木代!”
木代奇怪,抬头说:“啊?”
霍子红紧紧攥住楼梯把手,脸色青一阵白一阵,嘴唇微微颤动着,好一会儿才强笑着说:“没什么,看完罗小刀回来啦?”
木代回答:“嗯。”
霍子红目送她离开,听到足音一路往上,木地板上轻轻的压动,然后是关门声。
她腿上一软,险些坐倒在楼梯上,炎红砂一把扶住她,她抱着炎红砂的胳膊,像抱着救命的稻草,一直念叨:“红砂,你看见没有?看见没有?”
霍子红眼前渐渐模糊。
木代有白头发了,刚刚,她头一低,披散的发间,发根处,露出丝丝的白来。
自己四十多了,保养得当,都还没有白发,木代才多大点的姑娘?
半夜里,霍子红睡不着,惦记着木代睡的好不好,起身找着了房门钥匙,屏住气,极轻地打开门。
刚一推开,触目所及,险些叫出声来。
木代没在睡觉,她搬了把椅子在窗户前头,抱着膝盖,坐在椅子上往外看,月光透进来,她身前身后,还有她自己,被照的银亮。
听到声音,她转过头,说:“红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