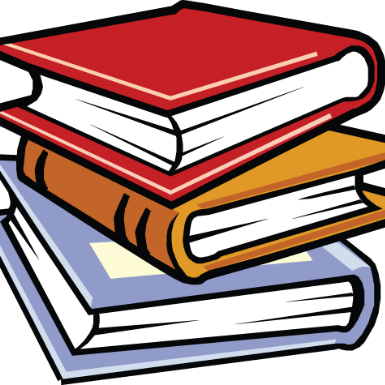蒙先生似乎看出了我心中的疑惑,干咳了一声,笑道:“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我无儿无女,老来自然只有跟随战儿养老,但放了一辈子的山,手头也有点积蓄,经常有些小蟊贼把主意打到我的头上,而且当地藏民中,也有一小部分不法之徒对我们不太友好,为保安全,只好做了一些准备。”
这个说法虽然有点牵强,但也还算说得过去,再说了,人家有钱爱怎么整就怎么整,我们也管不着,当下随着蒙战转了一圈,又到书房去参观了蒙先生收藏的一些古玩书画,我自己往日也喜欢玩玩古玩,多少还懂一些,见那些东西虽然大多是西藏具有代表意义的收藏品,但却没有什么大价值,全是市面上一些比较普通的玩意,没什么特别扎眼的,随口夸了几句。
正准备离开书房,却忽然一眼看见在书架上面供着一个纸人,这纸人完全就是照着蒙先生的样子画的,那鼻子那嘴,那眼睛那下巴,那头发那胡须,连额角上纹的那只小蚂蚁,也都一模一样,只是比真人小了几号而已。
这一发现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指着那纸人问蒙战道:“一般人家都会供个菩萨观音什么的,你们东北也有供五路大仙的,这怎么会供个纸人呢?”
我这一问,蒙战的兴趣也来了,笑道:“不要小看这纸人,这其中还有个故事,而且这事说起来还有点长,得从有一回叔叔去寻阴参说起了。”
老六急忙摇书打住道:“别介,你还是从他采阴参回来后,纸人张给他治好了病说起吧!前面那段你叔叔都说过了。”
蒙战“哈哈”就笑,说道:“我就猜到了,叔叔老拿那事来教育人,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吃过人肉似的。”接着话锋一转,说道:“不过这纸人,还真跟这事儿有关系。”
“前面的事你们都知道了,我就不说了,我就从张叔把叔叔的病治好了后开始说。张叔治好了叔叔后,在我们这小县城里的名声那就出去了,很多人找他治病,可张叔根本就不出手相助,不管是谁,不管是什么原因,就是不出手,甚至因为这些事情,遭遇到了一些当权人物的刁难,要不是叔叔一直在暗中维护他,只怕在那小城市他都待不下去了。”
“一直到黑子出了事,张叔才再次出了手。”说到这里,又加了一句:“黑子你们都看见了,他不怎么说话,人很闷,但很正直,打得一手好枪法,可左右开弓,百发百中。”
“黑子自幼父母双亡,成了孤儿,一直都随着张叔,亲如父子,行为上也受张叔影响甚深,做事稳妥,性格低调内敛,甚少出什么差错,那天也不知道怎么的,莫名其妙地就出了事。”
“那天我和黑子也不知道哪来的兴趣,想起了去打猎,哥两个一人扛了条猎枪,就进了山。但咱哥俩从来也没有过打猎的经验,在大山里转悠了半天,愣是一根鸟毛也没打到。”
“也是活该出事,本来兄弟俩就是玩的,没打到东西也没觉得有什么不爽,谁知道就在即将出山的时候,忽然从树林里飞出一大片乌鸦来,黑子一时兴起,‘砰’地就是一枪。”
“那散弹猎枪的攻击范围甚广,这群乌鸦也很是密集,这一枪足足打下来有十几只之多。虽然说乌鸦这玩意不怎么吉利,但我们俩一向胆大包天,也没拿这些鸟儿当回事,当下就将那些乌鸦拣了拣,有比没有好嘛!”
“谁知道其中一只竟然没死,但也飞不起来了,就顺着地面直溜,我和黑子就追了过去,那只乌鸦一直溜到一座坟头上,不再跑了,反而转过头来盯着我们看。”
“这大山里猛地出现一个坟包已经够瘆人的了,何况这乌鸦还蹲在坟头上,我看见乌鸦那泛着邪光的眼珠子,心底忽然莫名地有点发毛,手里的散弹枪虽然对准了那只乌鸦,却始终没有敢开。”
“黑子这家伙别看平时闷声不吭的,实际上胆子比我还大,见我不开枪,伸手就把散弹枪夺了过去,对着那乌鸦就是一枪,由于距离近,散弹枪威力又不小,乌鸦一下子被弹珠打飞出去好远,坟包上的草皮也被掀翻了一大块。”
“谁知道这一枪可惹了大麻烦,那坟包竟然只有上面一层草皮,里面全是蛇,拥挤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大蛇团,黑子一枪不仅掀开了一块草皮,还轰烂了好几条蛇,支离破碎的蛇身散落了一地。”
我听到这里,浑身鸡皮都起来了,这场景确实诡异,荒林之中,一座孤坟,坟头上蹲只乌鸦,枪声响起,乌鸦惨死,坟上的草皮被掀起,露出一坟包的蛇来,这太像电影里的情节了,只应该存在人类的想象力之内,实在不应该真实地在人间出现。
蒙战继续道:“虽然我们兄弟俩一向胆大包天,当时那场景我们俩一见也有点发蒙,吓得乌鸦也不要了,对看一眼,拿着枪转身就跑,一口气跑到山脚,上车一发动就窜回家了。”
“一路上,兄弟俩默契得谁也没有提那事,但我看黑子的脸色,蜡黄蜡黄的,很是难看,我自己的脸色估计也好看不到哪儿去,一直到家,都没有发生什么事,我本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谁知道当天晚上,就出了事儿。那天我就有预感,总觉得事情不大对劲,所以就没回家,就在黑子家住下了,正好张叔和叔叔去喝酒了,也不在家,我就和黑子弄了两个菜,哥俩也喝上了。”
“黑子刚喝两盅,忽然‘腾’地一下站了起来,‘啪’地一拍桌子,指着自己的鼻子骂道:‘你这小子,好生大胆,敢在我白常太爷的地盘上撒野,不给你点苦果子吃,你也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说完,竟然伸手揪住自己的耳朵,将自己摁在了地上。”
“我一看吓了一跳,不知道黑子这是玩得哪一出,也没敢出手阻止,急忙掏出电话来,就给张叔打了过去。张叔正喝着呢,听我这么一说,二话没说就把电话给挂了。”
“黑子这时候已经完全平趴在地上,脑袋奋力向上昂起,两眼发直,舌头不住伸缩,双手并拢合于双胯上,两腿也并在一起,正伸长了脖子拼命地在地上扭动身躯,努力向前游动,像极了一条蛇。”
“我再傻,也知道怎么回事了,黑子这肯定是中邪了,得在张叔回来前,先阻止住他再说,这样在地上游动可不是事儿,脖子昂成那样,谁吃得消啊!一想到这儿,我急忙上去想按住黑子,谁知道那家伙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一翻身,双腿一弯一扫就把我甩一边去了。”
蒙战说到这里,停了下来,看了我们一眼,这大夏天的,外面日光闪耀,骄阳似火,但我却浑身汗毛都竖立了起来,蒙战说得太吓人了。虽然我心中一再告诫自己,蒙战肯定是在说瞎话吓唬我们,但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总是瘆得慌。
老六估计也吓得不轻,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强笑道:“战哥,你就使劲吓唬我们吧!但别指望我们会相信,反正等会儿我们和蒙先生一对质就知道实情了,你们叔侄俩都有一个相同的潜质,可以去当说书匠。”
蒙战苦笑了下,说道:“别说你们不相信,要不是我亲眼所见,自己都不相信。”说完,咽了口吐沫,又继续道:“兄弟自幼练习技击,虽然不敢说能有多大能耐,身手也算敏捷,但就在我被黑子甩开,一翻身爬起来这会儿工夫,黑子竟然已经蹿到了门外,就用那个像蛇一样的姿势,游到了门前的一棵树上,脚已经离地有三四十公分了,还在继续向上移动。”
“我立刻扑了上去,死死抱住黑子的腰,硬将他从树上拖了下来,摁在地上。刚刚按住,黑子忽然阴阳怪气地说道:‘还不赶快松手,你小子也想倒霉吗?难道我白常太爷才几十年没出来走动,就没人把我放在眼里了?’我哪里敢乱说话,只好使劲摁住黑子,不让他乱动。”
“黑子一向没有我力气大,但那天完全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见我不松手,一扭之下就将我再度甩飞了出去。说实话,我连黑子的动作都没看清楚人就飞出去了,一头撞在了墙上,接着眼前一黑,我就昏了过去。”
“等我醒过来时,张叔和叔叔都到了,黑子则已经爬到了树上,盘在两截扁担粗的树枝上。”
一听说黑子“盘”在树枝上,我心起疑惑,看了蒙战一眼。蒙战见我看他,知道我的意思,点了点头,加重语气道:“你听得没错,是盘在树枝上,一条腿勾住一根树枝,另一条腿悬挂着,鞋子还掉了一只,就这样光着脚,双手依旧并拢在胯上,身子扭曲到最大限度,用肋骨和胯围之间的软组织,夹住另一枝树枝。”
说着话,蒙战伸手拿起书桌上的毛笔,在纸上简单画出一个扭曲到极致的人形来,将笔一丢,伸手指着道:“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却画不出那种诡异的气氛。”
我一看之下,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画中那人,腰几乎呈现出九十度的斜对折弯曲来,一腿勾一腿悬,头还奋力向上昂着,姿势怪异到了极点。虽然我知道现在有些玩瑜伽的能练到柔若无骨的程度,但那也只是极少数人,还得数年的苦练才行,但黑子怎么看也不像是个瑜伽高手,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
蒙战继续道:“张叔则坐在树下,拿着干篾黄,正在飞快地编扎,不一会儿就扎出一个纸人的形状来,随手拿起几张白纸,一支毛笔,半碗糨糊,几色颜料,就用手沾糨糊,刷刷刷将白纸糊好,拿起毛笔,想都不想,提手就画。”
“片刻过后,一个活灵活现的纸人版黑子就画了出来,只是小了几号而已。叔叔则赶紧递过香烛黄纸,米碗烛台,张叔点上香烛,燃起黄纸,跪下,边磕头边喃喃道:‘白常天龙大仙慈悲,小辈年幼无知,不识大仙神威,万望大仙慈悲为怀,放了黑子一马,特令黑子向大仙赔罪了。’”
“说完话,跌坐在地,口中念念有词,忽然喝了一声:‘疾!’一片黄纸旋转飞起,竟然飞到树上的黑子身边,从头掠到脚,削下黑子一缕头发,还割破了黑子的脚面。”
“张叔招手接住黑子的头发,拿起纸人,送到黑子的下方,几滴鲜血从黑子的脚面上滴落,正好滴在纸人背上。”
“张叔将那几根头发沾了沾血迹,粘在纸人头上,又伸拇指沾上血,分别在纸人的印堂穴、檀中穴、丹田穴、左右太阳穴、双手劳宫穴、双脚涌泉穴一共九处大穴上的位置各点一下。”
“这一系列动作那真是快如闪电,张叔双眼精光四射,面上神色肃穆,口中念念有词,腰直腿绷,双手如飞,简直和平日里那个反应迟钝、沉默寡言的张叔完全两样。”
“说也奇怪,张叔点完血迹,手一松,那纸人落在地上,就这么直愣愣地站着,竟然没有倒下,张叔又大喝道:‘还不向白常天龙大仙赔罪!’那纸人随之一呆,双膝竟然像活人一样缓缓跪了下去,对着依旧盘在大树上的黑子磕起头来。”
我听到这里,只觉得后背凉飕飕的,再也不愿意相信了,故意“哈哈”大笑了两声,给自己壮了壮胆子,才开口说道:“蒙大哥你说得也太玄乎了,纸人都是干篾黄编扎的,怎么可能弯腿跪下,腿一弯不就折断了吗?更加不可能还会磕头了。”
蒙战咂吧下嘴,也笑道:“我知道这事说出来也没人信,你们几个就当故事听吧!”伸出舌头舔了下厚厚的嘴唇,滋润了下,征询似的问道:“后面的事,还要不要听了?”
我点了点头,虽然不大相信,心里又害怕,但人都有一个特点,越是害怕越是想知道,越是神秘越是能引起人的求知欲,明明知道这些怪力神异不大可信,但还是想知道究竟还会发生什么事。
蒙战见我们几人都点头了,就继续道:“黑子盘在那树上,昂着头冷冷地看着张叔操弄这一切,一直没有说话,直到那纸人磕了好几个头,才阴阳怪气地说道:‘看不出你这老儿倒也还有几分手段,这份纸人附魂术玩得还真有几分火候,还夹带着替魂术,不过在我白老太爷面前,你也不用显摆了,这孩子倒也有几分韧性,被我折腾到现在连吭都没吭一声,罢了吧!这事就这么算了,大仙我也不追究了。’”
“黑子说完,忽然浑身一阵急颤,就像被人从身体里抽离了什么东西一样,然后整个人就像虚脱了一般,直手直脚地从树上掉了下来。”
“我急忙奔过去想接住黑子,但黑子毕竟也一百几十斤,又从那么高的树上摔下来的,力道不轻,虽然我胳膊拦着了,可惜没有托住,但被我这么一拦,下坠之势减弱了许多,黑子虽然摔得龇牙咧嘴的,毕竟没有太重的伤势。”
“那纸人却忽然软软地摊在了一边,就像被抽了筋一样,我好奇地走过去拎起纸人看了看,着手之处的篾黄,寸寸截断,全无相连之处,但外面的白纸却又丝毫无损,甚是奇异。”
“张叔和叔叔急忙过来扶起黑子,将他扶到里屋休息。黑子上了床,不一会儿就沉沉睡去,一直到第二天日上三竿了才醒转过来。但奇怪的是,我问他头天晚上的事儿,他却什么都不记得了。”
“后来这事不知道怎么又传了出去,张叔那纸扎店再也不得安生,什么达官贵人、黑道枭雄、商贾巨富、市井平民全都来了,求财的、求保命的、求升官发达的,什么都有,软求的、硬来的、威逼利诱的,什么手段都耍了出来。叔叔虽然在那一片有点影响,但也保不住张叔了,最后无奈之下,只好安排张叔和黑子来了米林,这里地方相对要偏僻很多,张叔又刻意低调,倒也过了段太平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