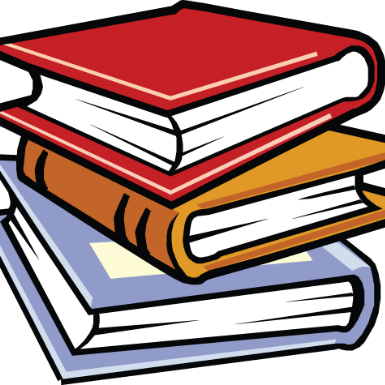时间是上午9点半,毛哥、鸡毛和光头齐刷刷坐在电脑前面,看视频框里神棍高高撅起的屁股——没错,是屁股,神棍正弯腰翻检什么东西,屁股撅的老高,恰好对准了摄像头,于是毛哥这头的视频很是有碍观瞻,光头冲电脑屏幕上打了一巴掌,就跟真的能打到神棍似的:“哎哎,你不会蹲下去翻吗?”
神棍嘟嚷了句什么,果然就蹲下去一些了。
毛哥则异常纳闷:“你居然能把你那麻袋都拖到网吧里去,人家就没当你是捡破烂的?”
鸡毛还在为神棍刚刚吓他的事恼火:“你不是这么早就老年痴呆了吧?这么诡异的事搁谁都印象深刻啊,真记不起来要去翻你的破笔记?”
神棍腾的一下回转头,恶狠狠瞪鸡毛:“哥一生都在追寻和记录诡异的事件,哪能件件都记得清楚?再说了,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本着严谨的科学态度,还是翻笔记保险一点……哎,岳峰呢?”
他此时才发现自己的听众少了一个。
光头嘴巴朝外努了努:“外头呢,给他女朋友打电话。”
神棍脸上露出羡慕嫉妒恨的复杂表情,然后继续低头撅屁股翻检笔记。
这一次光头和鸡毛没有对他的有碍观瞻提出异议,两人不约而同回头看外头的岳峰——他其实没有在说话,手机在耳边搁着,过一段时间便拿在手上重新拨号。
光头拿胳膊捣捣鸡毛:“苗苗会接么?”
“那是绝对不会。”鸡毛答的很肯定,“谁还没点骄傲啥的,搁我我也不接啊,苗苗那么娇气,肯定更不接。岳峰这是白费劲,太不了解女人了。”
“错!”毛哥斜了两人一眼,“岳峰这才叫了解女人。你都说了,苗苗那么娇气,你要是一通电话都不给她打,她不更受不了?岳峰最好就这么打下去,那头接不接无所谓,真打了99通100通了,苗苗的气也就消的差不多了。”
正说着,岳峰突然大踏步往台阶下走,看情形是朝什么人去的,鸡毛奇怪:“干嘛去?难不成苗苗回头了?”
“靠,不会真回来了吧。”光头到底还是不怎么看好他们,一听说又要旧梦重温,眉头都拧成了个疙瘩。
毛哥起身走到门边,朝外瞅了瞅,然后朝两人摆手:“不是,他认错人了。”
“苗苗都能认错?”光头鄙夷。
鸡毛鄙视光头:“那能是认错苗苗吗?铁定是错认成棠棠了,打赌,十块。”
光头看毛哥表情,断然回绝:“我是好青年,不参与赌博。”
鸡毛冷哼一声,正准备损他两句,音箱里传来神棍慢条斯理的声音:“我说,你们还要不要听专家回忆那过去的故事了?”
三人一起回头,神棍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翻腾好了,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手里还捧了一本本子,封面的图案是赵薇版还珠格格,封面已经起角,看出是有些年头了。
神棍清了清嗓子:“这事吧,是我游历到青海的时候听说的,大概是三四年前的时候。”
————————————————————
08年头上的时候,我游历到青海省德令哈市,德令哈你们知道不?在柴达木盆地北部,海子有首诗,叫《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算了,你们这群文盲,跟你们说你们也不晓得。
当时吧我在德令哈下面一个镇子里候车,准备倒车去西宁,那时候德令哈的新车站还没修,汽车站破烂的很,车子久久不来,我和三四个等车的人在站口蹲着啃茶鸡蛋,里头有个老头,之前在德令哈劳改农场待过。
知道青海的劳改农场不?这又是老一辈的事了,你们年轻人不晓得。我这么跟你说吧,青海这地方,又荒又偏,历来就是流放犯人的地方,58年□,被逮捕判刑和劳教的人激增,监狱、看守所人满为患,那时候下了个文,要在大西北广建劳教场所,单单青海省,3年内就有二十几万人从全国各地被送过来。其中不少劳教分子、□啊,跟那些真正的犯人混合编组,同吃同住,青海这地方,高寒、缺氧,这些城市里来的知识分子本来就适应不了,又要从事重体力劳动,大批人被饿死、冻死,虐待死的也有,正好又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死人那更是大片大片的。
这事吧也就发生在过后几年的时间,岁末大寒的时候,有一天,劳改农场里死了两人,怪了,不是饿死也不是冻死的,是叫人掐死的。一来那年头死人是常事,二来吧也没个摄像头啥的,警卫查了半天,查不出个子丑寅卯,再加上寻思着关进来的人都不是善茬,集体关起来饿了两天,训了一顿,也就不了了之了。
给我讲这事的老头那时候才二十来岁,他姓郭,就叫他老郭吧。老郭对这事挺上心的,原因是他跟其中一个处的还不错,那人也大方,家里给寄了炒面,他还分老郭一口。老郭说当时他就觉得这事蹊跷,那人是个老实头,不可能给人惹事的,怎么就叫给掐死了呢?
发现出事的时候快晚上了,一时间找不到埋尸的,就先搁场部的草棚子里,差人守着,老郭争表现,自告奋勇去了,场部的领导还让他给登记一下死者信息,整理一下死者遗物,这一折腾,叫他发现两件不对劲的事来,第一是好巧不巧,这死了的两人,出生的月份和日子都一样;二是这两人后颈子上,都叫人剥掉了一块皮。
老郭当时挺害怕的,但是那年头,不敢乱说话,也就掖着不讲,后来埋尸的人来把尸体拉走了,让老郭回自己的棚棚去,老郭心里有事,寻思着外头走走透透气,就绕了远路,这一绕,就在一柴垛子后头发现农场里一老头在吃独食。
先头我也说了,那几年全国都缺粮,这些劳教劳改的人更是饿惨了,寻空就出去挖草根挖地衣,有些还偷偷宰了公家养的猪崽子羊崽子,吃的时候不敢叫人看见,跑的远远的,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跑出来吃独食。
当时那老头生了堆火,茶缸子搁火上头,好像在煮肉汤,味道香着呢,要是别人的话老郭兴许还讨一口喝喝,一看是那老头,立马就绕开走了。
这是为啥呢,因为这老头有一身脏病,说不清是什么病,反正就是特严重的皮肤病,全身的皮发黑,血管都找不着,大片大片的溃烂,淌黄水,那臭味,远远的都熏人,他的东西再好吃,老郭也嫌弃不是?所以他不声不响就走了,那老头都不晓得他来过。
老郭走了有十来步,听到那老头在后头怪叫,嗓子里嗬嗬的,跟狼似的,他回头瞅了一眼,看到那老头围着那茶缸子手舞足蹈的,跳一阵子就跪下来磕个头,嘴巴里咕噜咕噜的,也不知道念叨啥。老郭当时还吐了口唾沫,心说这老头有病,能吃上点东西都乐成这样。
老郭没把这事往心里去,后来吧他表现好,又会识文断字,场部的领导提拔他去档案室打打下手,有天把农场里的一部分犯人往格尔木农场调,犯人得过来领介绍信啊条子什么的,这老头也在,档案室一堆人见着他都惊着了,那年头病死的人多,都寻思着这老头一身脏病,保不准哪天就蹬腿了,谁知道没大夫没吃药的,他居然全好了!
全好了你们能想象吗?那一身烂皮,跟换过似的,气色也好,笑呵呵的,问他怎么治的也不说,就说是自己命大。
老郭给他开的介绍信,翻档案的时候看到他生日,我估摸着你们都想到了,跟死的那两人是同样的日子月份。老郭觉着不对劲,但是他又说不出什么不对劲,就眼睁睁看着那老头乐呵呵走了,也不知哪去了,总之后来就再也没见过。
当时吧我们三个人在车站听老郭讲的这事,都猜说是那老头茶缸子里煮的是死的那两人的后颈子皮,那老头不是还围着茶缸子跳舞吗,不是还嘴里咕噜咕噜的吗,可惜了老郭没近前去看,那保不准就是什么仪式什么咒语,玄乎着呢。
老郭后来离开农场,被安排去铁路上当扳道工,一晃眼也几十年了,这事一直是他心头一疙瘩,总想寻个究竟。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他听到一个说法,当然说的人是当笑话说的,说是解放前,青海西陲有个不跟外界来往的独庄子,庄子里供巫医,治病都是邪法子。简单打个比方,你得皮肤病了,你就整个人,剥块皮吃了,病就好了;你得心脏病了,你弄颗人心来吃了,病也就好了,当然不是下肚就完了,中间有仪式有咒语,外人是搞不清楚的。最玄乎的是说能把人从死里给整活了,要行阴阳配,意思是要一男一女两个人,两人的出生月份日子都得跟要治的人一模一样,当然同年同月同日生更好。死而复生之后的头三年,每年都得再耗一对阴阳配。这个独庄子都是从外头骗人进来做药,有一次不晓得怎么的,让其中一个给跑了,带人过来寻仇,把这个独庄子都给灭了。
老郭寻思着,那老头没准就是独庄子里留下的种,所以还会使这套邪门法子,但后来也没人见过那老头,也就只能这么推测着。你们也知道,我到处探听这些个玄异的事,不管有没有真凭实据,先记下来总没错了,就算不是真的,听个新鲜也好,是吧?
————————————————————
毛哥他们听完,半晌没出声,鸡毛不知道是吓住了还是怎的,破天荒没有要死要活呼天抢地,岳峰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进来了,站在三人后头静静听着,末了问神棍:“所以这事,你也只是听说,里头再玄乎的部分,你也不知道了是吧?”
“去哪知道?”神棍找借口,“你没听说吗,独庄子都让人给灭了,要是还在,我铁定寻过去实地探访了。”
毛哥只觉得喉咙发干,他咽了口唾沫,抬头看岳峰:“假如这些都是真的,那陈伟和凌晓婉,恰好就是一对阴阳配,是吧?刚不是说阿坤弟弟,就是那个叫阿鹏的,骨癌死了么,你说会不会是阿坤领了他的尸体之后,弄什么阴阳配把他给整活了?不是说死而复生头三年每年都要再耗一对吗?那陈伟和凌晓婉算是撞枪口上了?”
光头点头表示赞同:“但是棠棠的生日跟凌晓婉他们不一样吧?那人打上门来找她,为的什么?”
岳峰沉吟:“可能是棠棠发现了这个秘密,威胁到他们,他们怕事情暴露。”
毛哥头皮发麻:“这丫头完了,这丫头死定了,那人把她绑峡谷里,怎么样都弄死她了,弄死了往山疙瘩缝里一塞一埋,谁能找着?”
几人在这头对答,声音时大时小,神棍那头也听不真切,只听到最后几句,冷哼一声很是嗤之以鼻:“要我说,在尕奈毁尸灭迹最容易了,你们那不是有天葬台么?死人往天葬台上一丢,上百只秃鹰掀过来,肉丝都给你吃干净了,秃鹰吃不完山梁上的野狗过来啃,听说山梁上的野狗也吃惯死人肉了,眼珠子都是血红血红的……”
岳峰心头一震,看毛哥他们时,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变了脸色。
末了是毛哥开口:“这样吧,岳峰,你和光头带上水、干粮和装备进一趟峡谷,尽人事看天命,尽量进到不能进为止,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丫头。我和鸡毛去天葬台……”
话还没完,鸡毛一张脸已经变的跟白纸差不多色儿,说话都打颤儿:“我……我不去天葬台,那头……土……土都是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