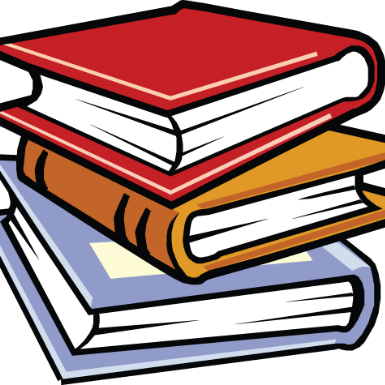车经过了新修的江桥,开去江北又开回来,李燃说,九点钟江桥的主灯就关闭了,还好赶上了。
必胜客还没关门,但他们都吃过晚饭了。李燃说,也没什么好吃的,当年只是因为省城像样的连锁餐厅只有必胜客,所以他觉得带见夏去必胜客自习很高级,人小时候都很傻,对吧?
而且,他说:“必胜客把沙拉塔取消了,你知道吗?我就那么点拿得出手的才艺了。他们还给我取消了。”
陈见夏一直偏着头看窗外,半晌,问,你想吃点辣的吗?
李燃愣了一会儿。
他一边将车子掉头一边说:“记得学校对面那家吗?”
“串串?”
“嗯。不过我上次去的时候是半年前了,老板说要回老家了,不知道现在还开不开了。”
见夏笑:“要碰碰运气吗?”
“走!”
开到一半,有什么缓缓落在挡风玻璃上,陈见夏凑近了看,“下雪了?”
她看得出神,伸出手,轻轻把掌心贴在窗上。
“是初雪吧?”李燃将副驾驶那一侧的窗子缓缓降下来,温柔地说,“那你摸摸。”
落雪要怎么摸?蠢狗。
陈见夏将头靠在车窗边缘,雪星星点点洒在她脸上,轻柔冰冷地吻着她滚烫的脸。
陈见夏,你摸摸雪。
走进人声鼎沸的店里,陈见夏惊觉自己太草率了,她身上的蓝黑色老式男子压格棉服和脚上趿拉着的粉色印花拖鞋都如此显眼,即便瞩目对象是一群高中生小屁孩,也实在难堪。
她这个时候才想起来诅咒弟弟陈至伟,干啥啥不行,当叛徒倒是敬业,刚才他哪怕演出一丝丝破绽,她也不会真的穿成这个样子下楼。
他们在小屋角落坐下,见夏将鞋子藏在垃圾桶后面。
老板还认识李燃,似乎他真的经常来光临,李燃问,老板,做到哪天啊?
老板说:“明天。”
他指了指窗子上贴的通知,加粗黑色记号笔手写着转租的联系方式,营业时间截止到明天。
两人一时都有些伤感。
“还真赌对了,”李燃落寞道,“明天可能真的吃不上了。”
“你是故意的吗?”陈见夏问,“给我写了一个错的银行账号?”
李燃玩着筷子:“你的确没赔我那双鞋,回家怎么都刷不出来了,废了。”
“所以银行账号是不是故意写错的?”
“你就是不会赔,每次都嘴上说得好听。”
“你故意写错想让我给你打电话?你可以直接朝我要电话,也可以告诉我你的电话,让我直接打给你。”
“我给你了啊,你打了吗?”李燃冷笑,“今天要不是我主动,陈见夏,你会找我吗?”
“我——”
李燃看着她。
这个人怎么不老的,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瞳仁清澈,映出她的谎言。
他们较着劲,直到老板端着两碗脑花出现,“不吵架不吵架,次老花(吃脑花)。”
梦回高一,陈见夏没绷住,笑出声来。李燃也笑了,说,先吃吧。
“老板,”李燃喊道,“我自己去外面拿啤酒了啊!”
“这么冷的天还要喝冰的呀?”老板低头算着账,已经习惯了。
见夏喊住他:“你一会儿找代驾吗?那……我也要一瓶。”
李燃扬扬眉毛,陈见夏毫不示弱地回望,李燃笑了。
她不想放弃任何机会告诉他自己长大了。
在上海最烦闷的那天,Simon为了保持身材坐在对面什么也不吃,她一个人大吃日式烧鸟。那仿佛便是她以为自己能袒露的极限了,在你不吃东西的时候我吃,在你维持原则的时候打破,我不会跟着你走,戴你想看的假面。
但她终究没有更深一步的勇气和动力去把那个整洁男人拉去地板砖油腻打滑的苍蝇馆子。
所以他们始终是陌生人。
他们都不是李燃。
陈见夏不饿,却很馋,她贪婪地享受着这份热辣和熟稔,两人一起吃得鼻尖沁汗,最后串串还是剩了大半桶。
老板来数签子,问,咋个嘛,不好次?
见夏连忙解释:“好吃。其实我们是吃饱了才来的,趁你关店前捧最后一次场。”
老板很受用。
李燃问得直接:“明天就关门了,以后也不做了,还关心这个干吗?”
老板忽然严肃,用四川普通话认认真真地说:“匠人精神。”
把他俩都说傻了,片刻后,三个人一起大笑。
这一次陈见夏说要请客,李燃没和她抢,然而站在收银台前,陈见夏一摸口袋——她居然连手机都没带。
李燃笑得极为欠揍,他大声问老板,多少钱啊?
然后凑到陈见夏耳边说:“一百二,一千五,五万。”
“五万我真的打给你了。”
李燃从手机调出付款码,说,你欠我的是这些吗?别以为吃个饭笑一笑,一切就都迈过去了。
陈见夏低下头:“我们之间有什么需要特意‘迈过去’的?”
“没有吗?”李燃不笑了。
老板举着扫码枪,说,你俩能不能把钱给了再吵?
他们站在马路边等代驾,李燃问,要不要进屋去等?
两个人喝酒都不上脸,脸红不是因为酒。
雪越下越大,陈见夏闭着眼睛仰着头,任它落得满头满脸,像个小孩一样往空中吐白气,李燃温柔看着她,也不再问她冷不冷。
“你在想什么?”他问。
在想豪车店里的女孩。那张漂亮得无法否认的脸。
那个女孩的身份,决定了这场夜奔是喜悦浪漫的久别重逢,还是背德离经的小人行径。
但陈见夏不敢问。
只是吃个饭,他们只是吃了个饭,既然手都没碰一下,能不能让她先假装大脑一片空白,等这场雪下完。
见夏想起少年时在意他喜欢凌翔茜的事,一刻都忍不住,刚说过好了不问了,下一句又旁敲侧击问起来,最后把自己搞得身心俱疲防线崩溃,在大街上边跑边哭。
十七岁啊。十七岁想向三十岁预支智慧,三十岁却只想问十七岁讨一点点莽撞。
“李燃,你在想什么?”
陈见夏反问回去。
如果还喜欢她,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找过她?如果已经不喜欢她,留电话算什么,骗她下楼又算什么?
然而李燃没回答。
长大的不止陈见夏一人。
“你弟弟怎么对你的事儿一点都不清楚啊,”手机屏幕照亮他的脸,“代驾快到了。哦,我说什么来着,你到底跟你家里人有没有联系啊?”
“你有什么想问的可以直接问我。我人都在这里了。”
“……没有什么主动想跟我说的吗?”
“什么意思?”
“没别的话跟我说吗,如果我不问的话?”李燃问。
有,有那么多,明明三天三夜都说不完,但他们不是剖开胸膛展示心跳的小孩了,谁都想做那个先提问的人。
“比如?”
“比如,你后悔吗?”
见夏一愣。后悔?
她看着李燃,想从他眼睛里读出一些什么,告诉自己,是她小人之心想太多。
李燃的眼神是温和的,怜悯的,彻彻底底激怒了她。
有些话不需要讲太清楚,她瞬间明白过来。
他从来都不是善良赤诚的三好少年,只是对她而已,但这份好有时限——如果对象不是她,没有残存的温柔,或许那天他真的会空降下来霸道护短,无情戳穿他们一家人的拙劣把戏,当场逼他们转账。
她从一个局促的小镇姑娘变成识时务的说谎者,这是成长吗?
陈见夏,读书是为了求知,还是为了脱贫?
“你当年在南京……”她试图开口,被李燃迅速打断。
“我当年就是个大傻子,行了吗?”李燃冲得像被点燃了导火线,“你别跟我提我当年说了什么,恶心,你不会当真了吧?十七八岁谁不傻,演情圣演得自己都信了,陈见夏,你当时瞒我耍我那么久,我后反劲儿,后来越想越气,越想越气,不行吗?”
不行吗?
陈见夏无言。
当然可以。十年后她才被他指着鼻子骂,也只是骂了这么几句,好像终于还掉了什么,比五万块钱还重要的东西。
“银行卡号不是我故意抄错的,我是看见你,太生气了,一糊涂抄错了,你以为是找借口联系你?看在老同学的份儿上而已。那女孩是我女朋友,漂亮吗?脾气是有点差,但我喜欢。”
“嗯。漂亮。”她点头。
见夏半低着头,盯着自己的丑拖鞋。粉粉的底色,印着蓝色的丑陋的卡通熊,材质不是真的纯棉,外表起球,里面都是假绒。好丑。
“……陈见夏。”
见夏抬头,安然看着他,“真的漂亮。飞机上我就看见了,先看见她才看见你的。非常漂亮。”
“陈见夏!”
李燃忽然朝她伸出手,见夏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本能后退躲开,脚从棉拖鞋滑出来,袜子踩进雪里,从脚底冷到心里。
“您好,尾号0531的机主吗?”
代驾匆匆赶来,从代步小车上下来,整个人热腾腾的。
李燃没回答。
代驾往四周看了看,整条街上只有这两个人,他困惑地确认了一下手机订单,再次问,您好,您叫了代驾吗?
大嗓门?在面前,李燃不得不答话按键把车钥匙递给对方:“你先上车。”
“您好,您看一下这是我的代驾证——”
“你先上车。”
愣头青代驾接过钥匙,还想说什么,被李燃的脸色吓回去了,推着小车奔去马路边。
“能让我搭个车吗?”陈见夏温柔问道,“我没带手机,自己叫不了车,虽然大家闹得不愉快,我也必须坐你的车回家,实在硬气不起来。”
李燃又想伸手拉她,“我话没说完,我刚才的意思是……”
“我很冷。”
陈见夏平静地重复了一遍,“我真的很冷。我想回家。你愿意再迁就我一次吗,让我跟代驾一起上车?”
“你真的长大了。”他说。
李燃轻声说,听不出情绪,“你以前总莫名其妙的,第一次来吃串串,就因为我说我认识二班很多学习好的人,你突然就跑了,跟背后有狗撵你似的,招呼都不打一个。后来才知道是回宿舍学习了。……我刚才是真的想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
见夏跺跺脚,不接话:“我们到底为什么不能上车说?”
“因为我在这个地方说错话了,我想在这里把它扭回来。”
就像你一天跑我们教室三次折腾那两台CD机?当时看似无厘头,现在回想起来,倒是极为坚定自洽——恩怨当场解决,李燃要的只是他自己痛快。
那时候陈见夏只是个给他造成了一点困扰的陌生女同学,他要解决她。
后来他给了她许多温柔的等待,迟迟不回的短消息,绵延一个月也理不清楚的小别扭……现在一切都回到了最初的时候。
“我不要。”陈见夏坚定摇头,“我上车去了,除非你把我轰下来,那我的确没办法。”
她朝着已经发动的车走过去——依然坐在了副驾驶。
李燃只能坐在后排,一路无言。
到了陈见夏家楼下,李燃说我送你上去吧,你们楼下太黑了。
“不要。”
不是不用了,是不要。李燃听得懂。
“你这么多年也没少谈恋爱吧?”李燃忽然没头没脑冒出一句,“没别的意思,一种感觉。”
驾驶座上的代驾尴尬得像要试图原地融化焊进方向盘,假装自己不存在。
“嗯,”陈见夏终于回头,看着他,“学到了很多。”
陈见夏回到家,轻声敲门,没有用,最后只好按门铃。
小伟果然戴着耳机在打游戏,门铃惊动了郑玉清,见夏应付了她几句,只说自己去透透气,郑玉清看她一身打扮也的确不像出去“鬼混”的样子,放下心来,只埋怨她大晚上抽风。
见夏从沙发上捡起手机,看到两个来自公司的未接来电,四条新微信,一条短信息,来自李燃。
“你进家门告诉我一声。”
她回复:“安全到家了,谢谢你。”
陈见夏想问他正确的银行账号到底是什么,琢磨了一下,决定算了。他自己都说是他盯人的举动让小女友吃醋了,故意贴过去找郎羽菲的碴儿,她又何必为了争一口闲气重新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人穷志短,前方还有一块门静脉阴影笼罩着,她已经无耻过一次,不打算因为今晚挨了挫就装清高。
陈见夏站在窗边,看见楼下那辆车始终亮着车灯,没有走。
但李燃也没有继续给她发信息。
陈见夏隐约猜到了他在等什么,就像今晚他一再重复的那样:陈见夏,你没有什么话要主动跟我说吗?
她看着新家的白色塑钢窗。小时候,到了这个季节,无论学校教室还是普通居民家家户户都会着手封窗子,白色胶带一层贴一层,封得齐齐整整,只留一两扇用作通风,否则呼啸的北风会从每个缝隙钻进来。她在振华做劳动委员的时候也指挥大家封窗——这几乎是各种校内劳动里同学们最喜欢做的事情了,有季节更替的仪式感。
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不需要了。和新型塑钢窗一样,人也活得严丝合缝。
雪越下越大,许久许久之后,车开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