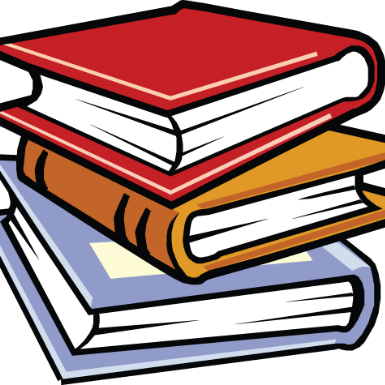霍子红忽然压低声音:“我问你啊,你跟罗韧,有没有发生过关系?”
木代脸颊有点烫,下意识摇头:“还没。”
霍子红吁了一口气:“还想提醒你呢,我是觉得吧,现在婚前发生关系挺普遍的,但是女孩子,还是要做好防护,万一冲动起来,你记得要让他用套,我看你还是个孩子呢,你要是那么早就生一个,带起来也够呛的。”
木代一直点头,没告别,也没说那些会让霍子红多想的似是而非的话。
如果万一真的回不去了,以后红姨想起她,想起和她的最后一通电话,就不会是泪水连连的生离死别,而都是亲昵私密和家庭的话题,像母女间不外道的温暖和贴心的秘密。
挂了电话不久,郑明山忽然打来,说:“我安排了之后,想着关心一下进展,就给神棍打了电话——木代,你是要跟罗韧结婚了吗?”
结婚?木代吓了一跳,下一刻反应过来:是他们之前在车上,畅想的封印凶简之后的打算,神棍也是呱啦呱啦嘴巴大,八字还没一撇的事,就跟郑明山说了。
“还让我务必参加婚礼,说地点都订好了,在离丽江不远的古城。”
木代哭笑不得,含糊着答了句:“可能吧,只是暂时……有这打算。”
郑明山和霍子红完全两个风格:“挺好,没事,大胆的结。罗韧要是对你不好,我帮你收拾他。”
木代咯咯笑。
郑明山感喟:“不是的,真的,师父吩咐过的。师父跟我说,你这小师妹挺孤单,从小就被抛弃,住在收养家庭,一直小心翼翼。将来要是嫁人了,做大师兄的得像个娘家人,该护着就护着,半点也别让——我就是没想到,这一天说来就来了。”
“定下了日子告诉我,一定到。”
电话打过,木代把卧室里的窗户开到最大,背贴着墙壁横劈下一字马,然后缓缓倾前下腰,下巴枕到交叠的手背之上。
这其实不是最好的时候,前路叵测,风浪诡谲,但心情像是踮起脚尖,站在风眼,前所未有的平静,如同银碗盛了晶莹雪,又像白马渐渐隐入无边的芦花丛。
一直以来都有心结,从小被抛弃,没有血缘亲人,被人收养,活得永远收敛,可是现在,站在这里回望,忽然可以淡淡一笑,说,那些所有的不顺,都是小事情。
现在就很好。
门响,曹严华不知道进来干什么,一眼瞥到她,哼了一声,说:“我小师父又在显摆自己韧带好了。”
木代笑出声来,低下头,长长的睫毛拂在手背上,痒痒的。
是的,现在就很好。
曹严华鼓起勇气,战略迂回,先给青山拨了电话。
青山在县城的工厂打工,接电话时,声音恹恹的,似乎也不大记得被附身时发生的事。
说:“亚凤跑了。我就知道,没这样的好事的,那么一个好看的大姑娘,哪能看上我啊,上赶着要和我结婚,结完就跑了,也不知道图个什么。”
“找了吗?”
“找了几次,找不着。有人说,跟外国人跑啦,后来我就不知道了。”
外国人?说的不会是猎豹的手下吧,曹严华岔开话题:“我爸妈还好吧?”
青山说:“大墩儿表哥,你不知道村里拉线了吧?才拉的,有电话了,你打回去呗。”
按照青山给的号,一键键点下数字,最后拨号的时候,手心都汗湿了。
通了,那头传来带着浓浓鼻音的土话:“啷个撒?”
“我,大墩儿……”
木代他们忍着笑,旁观了曹严华脸色转白、转青、险些转黑。
——“是上过房敲锣,那都多少年的事了,翻不过去了是吗?”
——“不是打电话朝你要钱的,我有钱,自己有饭吃!”
——“谁死在外头了?我好的很。拔巴你咋这么记仇呢?”
——“金花嫁不出去,怪我咯?她都出去打工那么多年了,人自己有想法,都多少年了你还抬不起头,至于吗?”
……
然后就没然后了。
揿了电话,曹严华瞪看着他的所有人,忽然来了气,跳脚大叫:“不打了,就当我死外头了,不打了!”
气咻咻去洗手间,甩门,砰一声响,隔壁房大概都听得到。
看来,不是所有的浪子回头,都能圆满收场的。
一万三想了好久,该给谁打呢。
没亲人,五珠村荒了,打电话给那些自己坑过的人,未免太矫情了。
末了,他去到门外,蹲在走廊里,拨了张叔的电话。
张叔说:“呦,这谁啊,这不江老板吗?还知道打电话,太感动了,你等会啊,我吃块肉压压惊。”
半大老头子了,说话还这么损,都常年上天涯学来的。
也不知道说什么,随便问了几句,店里生意好吗,进货价贵吗?有些卖家报价特低,十有八九是假的,别急着进,旅游景区,人杂,进店消费的,有客人,也有冒充客人下手切钱包的,一定要带上眼,多注意。
张叔觉得不对劲:“你唠叨这些干嘛?转性了?”
一万三说:“没什么,叔,要是我……不回去了,我那些东西,你就扔了,下次,招个比我靠谱的人……”
张叔说:“我怎么越听越不对呢,不回来是怎么回事?小兔崽子,你可得把话说清楚了。”
一万三心里有点难受,吸了吸鼻子,说:“没什么,就是这么一说。”
以张叔常年混迹天涯的机警和脑洞大开的程度,是断不会相信他这托词的:“一万三,你该不会是……得绝症了吧?”
“是早些年在外头落下的病根儿吗?我就说,你那小身板,平时也不注意,拼命往死里霍霍,人家曹胖胖比你壮,还每天起来跑圈压腿,你呢,锻炼过没?”
一万三没吭声。
“你倒是吭气儿啊,怎么个情况?医生怎么说啊?一万三,兔崽子,在听我说话没?我跟你说啊,有事要讲出来,大家伙有商有量地想办法。”
“是不是医药费贵啊,没事,我身上还有点钱,我跟老板娘说说,当初一万三千块,她都帮你还了,为你这条小命,再补贴多点,也有可能的啊。”
一万三忽然哭出来,咬着牙,不出声,抬起袖子,擦掉眼泪。
张叔还在那头一个劲追问,一万三清清嗓子,说:“不是,叔,屁事都没有,我就考验一下你对我的感情……”
于是,这曾经一度温情脉脉的电话以张叔的破口大骂和一句“你要敢回来,我敲断你的腿”告终。
虽然被骂了个狗血喷头,但一万三的心情,却出奇的不错。
回到房间,看到炎红砂拿酒店的小梳子在给曹解放顺毛,曹解放一脸的陶醉,像极了解放前压迫劳苦大众的地主老财。
一万三一屁股坐到炎红砂边上:“二火,打过电话了吗,给谁打的?”
“没人打。”
“你家里人呢?”
炎红砂小声说:“没家里人了,都死了。”
“就没别的亲戚了?”
“那种十年八年都不联系一回的,我干嘛打过去,我有那功夫,不如给解放顺毛。”
她倒是挺想得开的,一万三忽然有点佩服她,红砂身上,有一股近乎粗犷的侠气,说“我干”时,说的最干脆,喝酒时,也喝的最利落。
罗韧的电话打给了聘婷。
聘婷收到电话时,高兴坏了,说:“小刀哥哥,你很久、很久、很久,没给我打过电话了。”
一连说了三个“很久”。
罗韧说:“是很久了,你病了很久。”
聘婷沉默了一下,说:“病好了之后,很多事情就不一样了。”
罗韧笑:“还在吃药吗?”
“在吃。何医生说,最好巩固一下。”
“我房间的床头柜,抽屉下层,最底下,有一张卡,密码123456,里头大概有一百多万,记不大清楚了。”
“你拿上,为自己打算,进学也好,置产也好,自己规划,从现在开始,立根、立本。叔叔不在了,郑伯年纪又大,你要学着担起责任。”
聘婷沉默了好久,说:“我知道了。”
她从来就是个聪明的姑娘,含蓄、害羞,习惯暗示和话里有话,也听得懂别人的暗示和话里有话。
她换了个轻松点的语调:“我想以后自己开画室,所以可能会找一家国外的好点的学校进修,小刀哥哥,到时候你会来看我吗?”
“争取吧,去不了也会给你打电话的。”
聘婷忽然有点感伤:“小刀哥哥,小时候,我们老在一块儿玩,以后,会越来越疏远的吧?”
罗韧回答:“每个人都走在人群里,你走的离我远了,就会离另外一些人更近了,这是好事情。”
第三天的傍晚,夕阳血一样红,距离七七之数的到期日还有四天。
押车的神棍,就乘着这一抹夕阳的余烬进了通县,在酒店门口下了车,对前来接应的大堂服务生视而不见——当然,也可能是服务生觉得,这位肩挎无纺布袋,眼镜腿用线绑着,脚边还放了那么大一个破箱子的人,阖该是送货去工地的。
神棍给罗韧打电话,说:“小萝卜,我到啦。箱子沉,你们是不是下来接应一下啊?”
一边说,一边仰着头往楼上看,这酒店楼层真高,外窗的玻璃被夕阳映射的闪闪发亮。
罗韧打开窗,探身看下去,看到神棍在楼底,长不过手掌,那个装好的箱子,像个安静的火柴盒。
他笑了笑,回头看屋里的所有人,说:“到了。”
神棍到了。
另外六根凶简到了。
回避不了的命运……也到了。
☆、尾声
这个晚上,气氛凝滞到真的像是战前。
罗韧利用网上的卫星地图,大致拢出了凤子岭的高空地貌,凤子岭形似巨大的凤凰鸾扣,其实并不确定这地势是否也隐隐带有封印的力量——但既然要在这里做最后一搏,自然还是遵循古制以来的某些原则,比如中轴对称、方正严整,最终选定的是凤子岭中心地带,也称“岭眼”。
他教神棍使用电击枪:“选那里,还有一个原因,万一出现最坏的情况,我们压伏不住体内的凶简,转而行凶的话,待在偏僻的地方,总比在人多的地方要稳妥——你要做个决定,是电晕了绑起来,还是……清理。”
边上的曹严华听到“清理”两个字,一颗心沉到胸腔发闷,拉一万三到边上问:“至于吗三三兄,至于要‘清理’吗?”
一万三沉默了一下,说:“我听起来也怪怪的,但罗韧考虑的确实周到,万一结果不好,五个人身上有七根凶简,谁知道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还是那句话,报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吧。”
会变成什么样子?有那么一瞬间,曹严华的脑子里忽然闪过一帧帧诡谲的画面,四寨山里,那个喉头处蒙着胭脂色琥珀的、满头白发四肢爬行的女人,还有项思兰变了形的胸腔,森森的肋骨,拱卫着一颗看得见的、跳动着的心脏。
神棍不想学:“还是别吧,刀枪哪能往自己朋友身上招呼呢?”
罗韧回答:“谁知道那个时候还是不是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