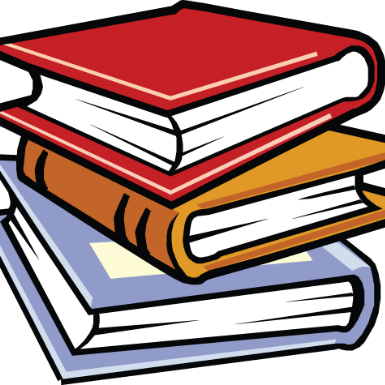陈见夏浑身发抖,步履不停,机械地噔噔噔下台阶,一直到没台阶可下才勉强停步。
她迷茫地抬起头看着楼梯折叠向上的之字形轨迹。
竟然就这么跑出来了?
妈妈偏心弟弟,姐弟吵架自己总是挨骂的那一个,也曾经几次三番赌咒发誓一定要离家出走,用实际行动告诉爸妈,再这么偏心下去就干脆别要这个女儿了,看他们到底会不会心疼。
永远只是想想,从没付诸实践过。
这一次,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她竟然头也不回地负气离去了!
四周安静得过分。见夏恢复理智,开始觉得身上有点凉。她没穿校服,没拿书包,上身一件单薄的长袖T恤,裤袋里只有二十块钱和一部小灵通手机。现在她要去哪儿呢?
可是她不能回去。她已经把事做绝了。
同学们不会明白她为什么这么伤心。大家没看成热闹,恼羞成怒,反而怪罪是她气量太小,反应过激。一个误会而已,解开了就好了,难不成于丝丝故意害你?心理太阴暗了吧?
这个世界多可笑。明明是无妄之灾,却要小心别还击过度,失了风度。
见夏想着,委屈得鼻酸,茫茫然掏出手机,用拇指摩挲着键盘,习惯性解了锁。
嘟嘟的等待音响起来时,她才回过神。
“喂?”李燃的声音从听筒传到见夏耳朵里,微微失真。
“……”
“陈见夏你有病啊,装神弄鬼有意思吗?说话!”
“我……我打错了……我本来没想打电话的……”见夏磕磕巴巴地回答道。
李燃轻笑了一声,没计较,更没提中午见夏把他一个人扔在运动场上的事。
“那我挂了啊。”他说。
“别!”见夏失声叫道,“你先别挂!”
李燃没说话,就这么吊在线上,呼呼的风声穿过听筒,从李燃那边吹进见夏一团糨糊的脑海。
“你……你下午还想出去玩吗?”她问。
李燃停了一刻才回答:
“不想。”
见夏噎住了。
半晌电话那边传来一串哈哈哈,李燃的声音满是笑意:“你早想什么来着?快,说几句好话给爷听听,你求求我,我就带你出去玩!”
陈见夏干脆利落地挂了电话。
过了几秒钟,和弦铃声响起,好像一个电击把见夏的心脏也激活了。
她忘记了头顶上那个教室发生的龃龉,一屁股坐到台阶上,把手机举到眼前。屏幕上“李燃”两个字不停跳跃着,像一只朝她奔来的大狗。
陈见夏人生中第一次控制不住地眉开眼笑,像一个打了胜仗的女王。
“我们去哪儿?刚才是在上课,我打给你你怎么那么快就接了?你们老师不会骂你吗?还有谢谢你的校服,幸亏咱们校服男女生都一样,被我穿了也看不出来,刚才真有点冷了……哦,坏了,我、我没带很多钱,只够坐车的,你先借我,我回去、我回去就还给你……”
李燃居高临下站在台阶上,双手插兜,耷拉着眼皮,一脸嫌弃地看着兀自絮絮叨叨的见夏。
他现在确定,这个女的绝对脑子有问题。
见夏说到一半就住了嘴,李燃的神情让她讪讪的,于是大着胆子上前一步扯了扯李燃的袖子,轻声说道:“我们先走吧,出了校门再商量去哪儿玩,走吧,走。”
“你到底怎么了?”李燃的嗓门在教学区的走廊里也不知收敛。
见夏说不出话。
不是她非要碎嘴,是控制不住。她想强行让自己热情积极起来。
在楼梯口静待李燃的几分钟,她能清晰感觉到勇气渐渐流逝——还是赶紧回去吧,班主任俞老师若是知道了,一定会对自己这种小家子气的行为颇有微词,不光受冤枉,还惹一身腥,多划不来;况且她跑了又怎样,大闹一场,最后还不是要坐回一班教室上课,未来还有三年呢,越晚回去越难收场,这不是明摆着作死吗?
回去吧,回去吧。
可是陈见夏不甘心。
只要走出这个教学楼,她就开弓没有回头箭了。
求求你,带我走,趁我重新变回那个可悲的陈见夏之前。
她抬起眼,一脸悲戚地望着李燃。
李燃被她的神情震了一下,忍不住弯腰揉了揉陈见夏的脑袋,像个当爹的哄孩子一样好声好气地说:“我不问了,走,走,咱们出去玩。”
没想到越是这样轻轻一拍头,一句话,反倒让见夏虚张声势的壁垒尽数瓦解,刚刚在众人围堵时缺席的眼泪,此刻哗啦啦淌了满脸。
苛待只会招致逆反,温柔却最让人脆弱。
李燃已经在心里骂娘了。他到底是为什么要招惹这么个事儿精啊!
女生一哭他就麻爪儿。面对蹲在地上呜呜哭的陈见夏,李燃颇有些狗咬刺猬没处下嘴的乏力感。
“有人欺负你了?”
“欺负”二字一出口,陈见夏就哭得更凶了。
“那我帮你揍他?”李燃也蹲在她旁边,有点好笑地问。
陈见夏摇头。
“别甩了,鼻涕都要甩我身上来了,”李燃摸了摸裤兜,掏出一包纸巾,抽出一张递给陈见夏,“正好还你。”
陈见夏接过纸巾狠狠地擤了一下鼻涕,顺手又把纸团还给李燃,李燃居然也接了过来,捏在手里才觉得哪里不对,低头盯着手心沾上的鼻涕,脸都快绿了。
就在这时头顶传来了脚步声。
“现在出来追有什么用,早就跑不见了,还是打她电话吧。”陈见夏听到了楚天阔的声音。
“我没有陈见夏的电话,”这个声音是于丝丝,“郑家姝,你们一起住宿舍,应该有她号码吧?欸,对了,她用手机吗?”
你才不用手机呢,当我买不起吗?陈见夏恨恨地咬了一下嘴唇,这个时候都不忘踩她一脚,于丝丝这个浑蛋。
“我也没有陈见夏电话。”郑家姝讷讷的。
几个人商量着往下走,见夏一抽鼻涕,立刻起身拉李燃,他本来还蹲在地上,被猛地一扯差点以头抢地。
直到那三个人走远了,见夏才从拐角的水房里走出来,歪头朝他们离去的方向张望。李燃走到她背后,张开右手掌,狠狠地拍在见夏的校服后背,从上抹到下。
“你干吗?”
“擦手,”李燃五指张开在见夏面前晃,“你沾我一手鼻涕。”
“这校服是你自己的,你忘了?”
李燃脸上立刻五彩缤纷。
“不打算跟我说说?”他看见夏正常了点,再次询问,“这么多人出来抓你,你是挪用班费畏罪潜逃吗?看不出来啊,不声不响地干了一票大的。”
陈见夏没接茬。
那三个人不急不缓地出来寻找她的样子,彻底让她不想回去了。
“我们走。”她回头看李燃,目光坚定了许多。
因为校庆,保安人员进出查得不是很严,他们很容易地就混出了校门。她义正词严地表示上次在西餐厅吃掉了三百块,非常不好意思,所以这次请李燃务必答应她AA制。
李燃点点头说好啊,然后目不斜视地路过公交站牌,穿过马路,扬手招了一辆出租车。
出租车。
李燃拉开车门,表情那叫一个天真无邪。
陈见夏硬着头皮坐到车上,计价器蹦得她心颤。李燃余光注意到,笑了,如沐春风。
“炫富有意思吗?”陈见夏咬着牙说道。
“有意思,”李燃大笑,“特别有意思。”
“有什么了不起,又不是你自己赚的钱,还不是靠爸妈。”
“炫富就是炫爸妈啊,我爸妈有本事也不行?爸妈是我自己的吧?可以炫吧?”
陈见夏简直要被活活气死。
但是不知为什么,李燃几次三番在她面前说自己五行不缺钱,说自己的鞋子一千五,请她吃很贵的老西餐厅,还故意打车吓唬她,炫耀自己爸妈有本事……她统统没觉得受冒犯。
这一切行为加在一起的杀伤力都比不上于丝丝轻描淡写的一句“陈见夏用手机吗?”。
见夏想不明白,愣愣地扭头看,看得李燃十分不自在。
“看什么看,想做我家儿媳妇?”
“你有病吧?”见夏闭上眼睛翻白眼。
“真的,有什么不好?好多人努力读书不就是为了赚钱吗?你当我老婆,就不用费劲儿考北大了。”
陈见夏哭笑不得:“别丢人现眼了。谁说读书是为了赚钱的?庸俗。”
李燃却没恼:“我当然知道有些人是真的热爱求知,但是也有人不是啊,而且,不热爱的恐怕占大多数吧?把一道题做一百二十遍,背诵一些屁用没有的课文,难道也是为了求知?不就是为了考个好大学,拿个好文凭,然后多赚点钱改变命运嘛。”
他说着,忽然凑近了见夏:“你呢?你是热爱科学文化知识,还是为了脱贫?”
“滚!”见夏恼了,一胳膊肘挥上去,被李燃挡下。
“你急什么啊,我又没真让你当我老婆,”李燃悻悻地扭过头看窗外,真诚地补充道,“你长得又不好看。”
陈见夏一头撞在车窗上。
她现在宁肯跪在于丝丝面前大喊“我是小偷”,也不想再跟这个五行缺心眼的家伙待在一辆车里。
“欸,师傅,靠边儿停,就这儿。”李燃忽然敲着车窗喊起来,付了款扯着见夏下车。
他们走进老旧的筒子楼居民区,在灰色的楼宇间穿来穿去。李燃眉飞色舞地讲着他小时候在居民楼里挨家挨户敲完门就跑的“光辉事迹”,见夏完全没听进去,忽然拉了他一把。
“干吗?”
“别走在人家晾的裤子下面,”她指了指头顶某户人家窗外伸出来的晾衣杆,“钻裤裆不吉利。”
李燃扯扯嘴角:“还说你读书不是为了脱贫,你看看你哪个地方有科学精神?”
见夏正要反驳,李燃突然眼睛一亮,盯着前方说:“到了!”
映入眼帘的是伫立在开阔地带的一栋白色建筑,砖石结构的主体四四方方的,居中高耸着一座钟楼,顶端不是十字架,而是一个月牙;正面墙体粉刷成了红白相间的横条纹,鲜明惹眼,在居民区的包围下,有种奇特的美感。
“这是……这是教堂?”见夏疑惑道。
李燃的目光明明白白表达了蔑视:“陈见夏,你读书也脱不了贫了,想别的辙吧。”
“你会不会好好说话!没完了是吧!”
“啥教堂啊,这是清真寺!”
“哦,”见夏有点惭愧,转而问李燃,“你是回民?”
“不是。”
“那你怎么会知道这个清真寺的?”
“我爷爷就住在这附近。以前爸妈没时间管我的时候,都是爷爷带我,所以这一带我很熟。这个清真寺1906年就建成了,真真正正是一百年前了,土耳其人建的。不过这个土耳其不是地中海那个狭义的土耳其,正确的说法是鞑靼人,我爷爷纠正过我,好像是跟谁有渊源来着,反正我没记住。”
没记住有什么好骄傲的,见夏好笑地看着他。
“不过盖到一半,工程师就死了,后来又换了人。建成以后这里做了一段时间的艺术学校,又改成清真寺,反正一百年间风风雨雨的,它也经历了不少吧,最后一次修缮是二十年前,听说是我爸妈结婚那一年。这附近住了许多回民,哦,对了,好多本地人来这里买牛羊肉,他们觉得回民吃的清真牛羊肉肯定质量好……”
李燃拉家常的语气让陈见夏听得入迷,像是又回到了那个谎称自己有百年历史的西餐厅。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自己来看。”
李燃示意陈见夏跟上。他们走近紧闭的大门,右侧墙壁上镶嵌着一块长方形的深灰色大理石碑,上面刻满蝌蚪一样的文字。
“建造过程都在这上面写着呢。”李燃指着它说。
见夏惊讶:“这你都认识?”
李燃沉默了一下,不好意思地笑了。
“不认识。”
在陈见夏即将闭眼睛翻白眼的时刻,李燃及时地补上了一句:“是阿訇给我讲的。”
“阿……什么?”
李燃笑了,“具体我真的不了解,好像还有个叫法是伊玛目?大概是神父、老师、尊者的意思吧。”
已麻木?见夏懵懵懂懂的,决定回去后自己查词典。
她索性坐在门前的石阶上,示意他慢慢讲。她整个上半身都伏贴在腿上,下巴搁在膝盖上,双手环抱,团成了一个球。李燃也跟着坐到了她旁边。
小屁孩李燃按遍了附近所有人家的门铃,没有一次被逮到,顿时觉得人生无趣,于是开始用小石子儿打这座新奇清真寺的彩色玻璃,被阿訇抓了个正着。
“我当时觉得我死定了,”李燃比比画画,“我只记得我爸妈不让我去招惹在街上烤羊肉串的大胡子叔叔,他们看上去就很厉害,而且的确总对我瞪眼睛。”
“那是因为你太烦人了。”陈见夏见缝插针。
“我以为这个房子里面全是烤羊肉串的,被抓到的瞬间以为他们要拿铁钎子把我也串起来。”
“真可惜他们没有。”陈见夏笑了,被李燃一个爆栗敲在脑门上。
“但是那位阿訇看起来和我爷爷长得特别像,区别只在于戴了一个白帽子。他没骂我,反而让我进了寺里。当然,只能在门口站着,里面那个宽敞的做跪拜祷告的大厅我是不能进去的,因为我不是回族人。这个石碑,”李燃指指背后的大理石牌,“就是他一句一句翻译给我听的。”
“可是今天怎么没开门?”
“这里马上就要动迁了,周围的老楼都要被拆掉,建成广场。里面的信徒也搬去了新建的清真寺,这个建筑要被改造成历史博物馆了。”
“那阿訇呢?”
“去世了。”
他们一同经历了一段奇怪的沉默。陈见夏并不会因为忽然听闻陌生人的死讯就跟着悲伤,但她扭头看着背后的老清真寺,忽然觉得它和自己一样孤独。
“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呢?”她问。
“散心啊,你不是不开心吗?”李燃站起来,跳下几级台阶,平视还坐在原地的见夏,“有什么不开心的就在这儿说,说完了就振作起来,重新回去跟傻×厮杀吧!”
陈见夏自然没当真:“神不会管我的。”
“会管的,”李燃笃定地点头,“相信我。”
相信你什么?
“真的,阿訇跟我说过,不开心了就看看塔尖尖上的月牙,多祈祷,少调皮,做个好孩子。”
李燃仰头望着直入蓝天的铁制白月牙,脸上扬起特别好看的笑容。
做个好孩子?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这么走味?陈见夏迷惑地看着李燃,却深深看进他的眼睛里。
见夏一直觉得李燃的眼睛和别人不同,倒不是多好看,却特别澄澈,黑白分明的,像婴儿一样干净。
很明亮。
能问出“你是求知还是脱贫”的缺心眼,是应该有一双这样的眼睛。
“你跟神都说过什么?”她忽然问。
李燃的脸立刻色彩纷呈了起来。
“这我哪记得啊。”他眼睛开始看别的地方。
见夏也没在这个问题上纠缠,“那你过去经常来这里跟神说话?现在也经常会来?”
李燃愈发不自在。
“咱不聊这些行吗,我一大老爷们,恶不恶心,肉不肉麻,”他一边说一边踢脚边的空矿泉水瓶,“你要是只想寒碜我,就别说了,走走走,去逛别的地方。”
见夏还没见过李燃窘迫的样子,一时心情好了许多。她笑着拉住他的袖子,轻声说,谢谢你。
然后就转过身,面对清真寺默立,双手交叉相握,闭上眼睛认真地祈祷起来。
祈祷些什么?陈见夏没有任何话可以跟神明讲。她心底从未相信过这世界上有神,更不认为阅尽人世悲欢的陌生神明会因为她临时抱大腿而帮她实现任何愿望。
神明不会让于丝丝和李真萍停止厌恶她,也不会让她忽然脑袋开窍到轻松上清华,甚至都不会给她一点点回学校的勇气。
她知道自己此时此刻即便再虔诚、再希冀、再充满勇气,真的踏入班级教室,面对大家各异的眼神,一定还是会丢盔弃甲。
这个过程她经历过太多次了。
即使再清楚“胜败乃兵家常事”,考砸了也一样心态失衡;即使再明白妈妈就是偏心的,下一次弟弟单独得到礼物她还是会酸脸子;即使楚天阔说再多次不要过分在意他人的脸色,她也还是会回过头去传一张道歉纸条,眼巴巴地等着李真萍和于丝丝给她一个笑脸……
为什么呢?为什么人懂得这么多道理,却一样也做不到呢?
日子还是要自己过的,要一天一天痛苦地熬。清真寺里有伊玛目引领大家洗涤灵魂,现实中的她自己,只能因为日复一日的失落与痛苦而“已麻木”。
这真让人难受。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陈见夏本来只想做个祈祷的姿态以回报李燃的好心。没想到,思绪越飘越远,越想越鼻酸,真的开始淌眼泪。
“你怎么又哭了?”
这次李燃的语气倒没有不耐烦,只是单纯的好奇。陈见夏羞赧,她从小就爱哭,自打进了振华,越来越爱哭。
“我只是觉得,说了这么多,”见夏抹抹脸,“自己都不知道想要许个什么愿,神也不会管我的。你个大骗子。”
李燃挠挠头,“那怎么办,那……那神不管,我管?”
见夏愣愣地看着他。
有那么一瞬间,她希望他是认真的。而她也真的愿意让他管。